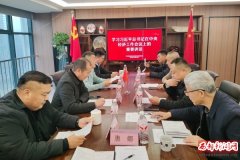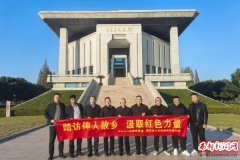悼 念 爷 爷
郭晓阳
半月前,爷爷还拄着拐杖到地里用绳子绑白菜,绳子勒得很紧,白菜就长得很硬实很饱满。听父亲说了此事,我很高兴,便想到,当是我在西安找的名医开的药方,抓的中药,对症见效。悬着的心就放下了。
然而,大约一周后,爷爷的病情开始恶化,时过不久,竟连亲儿子也不认识了,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父亲就去请了大夫,号脉诊断后,大夫说:“老人脉象微弱,大限将近,吊瓶输液,先维持着。”这时候,我正在西安搞展览,父亲电话说:“你爷爷怕是熬不到月底了。老人一生要儿要女,要子孙满堂,这时候你还外面干啥哩?世上的钱能挣完?事能做尽?赶紧回来!”我心一沉,交待了撤展的事,就急匆匆往回赶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层层浮现出自从我记事起,至今二十多年,我与爷爷点点滴滴的往事,还有我清晰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爷爷的慈善与威严。爷爷没受过很高的教育,但他一生严格恪守在农村根深蒂固的道德传统,自觉奉行世代因袭的“耕读传家”。我此生认识的第一个汉字,是爷爷握着手教我写的,歪歪扭扭的“郭”字,爷爷看着却乐呵呵的,喜欢地说:“我娃以后该是拿笔杆子的。”我此生记住的第一个成语,是爷爷兴致勃勃在祖居老屋新修了青砖门楼后,请乡里的书法名家题写的门头。一寸厚的木板,字刻得有棱有角,古朴庄重。那是九十年代末,乡亲父老已经脱盲,生活已不是特别艰难的岁月,连任第五届村支书即将换届卸任的爷爷,在六十五大寿那天,伴随着鞭炮声营造的喜庆气氛,亲手揭下了门头上的红布,指着扁额念到:“耕——读——传——家——”。
十七年后,当我勒上母亲为我缝制的第二根红腰带的二十四岁,迷信“本命年”里潜存着的,令人难以预料的福祸,就又一次拜访乡贤,请求预测运势。八月初,我取了斋号,并自撰了嵌名联:静思古训耕读传家自祖辈开元光前裕后;虚受新学著述载道从斯文典范正本清源。当年秋,我诚请我敬仰的文学前辈肖云儒、陈忠实、孙见喜老师,为我题写了“静虚书屋”。以文转运,于我只能如此。这都是缘于爷爷的道德风范,对我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到我这辈人,也应奉行“耕读传家”的精神传统,且至死不渝。
当乡亲们从大厅里抬出躺着爷爷的红色棺材,停在院里待时发丧的那刻,天开始下雪……哀乐奏响了,寒风搅着冬雪,越下越大。家里所有的亲人,全都跪在院里烧纸,为老人尽最后的孝道。主持葬礼的司仪握着话筒说:“吉时已到,准备发丧。路远地滑,要一口气抬到坟地,中途可以换人,但不能歇……”我家所有人就向抬丧的乡亲族人三叩首,以表敬谢感激之情。第二遍哀乐奏响,呜哇呜哇的唢呐声也接着响起,本家爷爷将一把纸钱撒向天空,送丧的队伍就出发了。
从平地到坡上,爷爷走完了无比艰辛也无比荣誉的八十五年。头顶是阴沉的天气,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湿柴草捂燃的烟。冒着风雪,一串一串的脚印一直延伸到老屋后土坡上的祖坟。这里埋葬着家族里五代的老人,祖宗为后辈儿孙,留下了永远的怀念。爷爷生前在这片土地上耕种,死后又回到了他生前耕种过的土地,完成了生命的最后驿站的归宿。
八十五年的春夏秋冬,八十五年的风霜雨雪,爷爷功德圆满了。而今长眠地下,阴阳两隔……爷爷,安息吧。
2018.12.5 红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