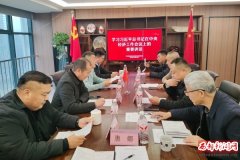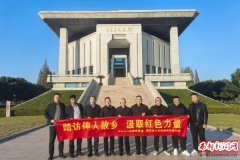每个城市都有树,每棵树都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穴位,这个城市的每条街道的每棵树,相连起来就是这个城市的经络图。
一个人气血的通畅在于经络,一座城风水的兴败在于树。
有谁在意过行道树被连根拔起时仓惶的哀嚎?人们会为一只流浪街头的小猫小狗洗澡喂食、看护守候,可谁会为一棵树的倒下默哀、掉泪?
曾几何时,树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人们在树上摆脱野兽的追赶;躲避洪水的侵袭;蒙蔽敌人的视线。在树上眺望太阳的初生,观察节气的变化,期盼爱人的归来,探寻族群的踪迹。
人们摘果充饥、钻木取火、造房、耕种、打猎,所有的一切都和树木息息相关。甚至当人们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祭祀庆典,都围绕着树展开。
那个时候,树就是人们的神灵。
现在人对树已是视而不见了。摆脱了最初对它们的生存依靠,情感投射。在现代人眼中,一棵树存在的意义和一块指示牌一般,任凭人们的调遣、摆设。
古老的树,美丽的树,芳香的树被起吊机们小心移走,送往大宅小院、室内屋外,那裸露在外的白森森的根须在颠簸的卡车上让人哀叹。
一夜之间,为了城市规划、道路扩建,那些原本好端端站着的树消失了。早上起来只留下一个个老碗粗的窟窿,在丝丝地冒着凉气。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的树像妈妈的头发一样又多又密。在风吹过来的时候,树上的叶子来回翻转,阳光照射的一面发白,照不到的那面发暗。远远望去,树冠像是绿色的金丝绒在左右摇晃。
伴随着树叶沙沙作响的,是孩子们踩着从树叶间隙投向地面的小光点上跳皮筋、打沙包。往往这个时候,在巷子的那头就有了一位推着小车卖冰棍或小镜糕的老婆婆吆喝着朝我们走来。
那时,树在我的童年中站成了一排温暖的回忆。像外婆手中的蒲扇,送去的不仅是清凉还是慰藉。
本来,树就应该和这个城市的建筑血肉相连,浑然一体。多少的老照片,记录的不就是这一个个动人的场景吗?
我们家离大雁塔很近,在一个中轴线上,只有两站路的距离。每次不管步行还是坐公交车亦或是自己开车,走在雁塔路上都很舒服。
虽然马路只有四车道宽,但两旁那满眼葱翠、繁茂旺盛的国槐,给它身后的大雁塔都增色不少。多少次,我站在路旁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身旁的国槐巍峨挺拔像忠心的士兵,庄严地站在两侧,拥簇着余辉中的大雁塔。此时的大雁塔王一样气定神闲、霞光万丈、气势磅礴,我的内心就涌动着对生命的美好赞叹。
忽然有一天,当我再次坐上公交车上时,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有些恍惚,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可说不上来。直到经过一个临时围起来的准备修地铁口的路段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路的国槐都被砍去了,为的是四车道变六车道,为的是修地铁口,让更多交通工具载更多游客到此一游。
再抬头望大雁塔时,没有士兵的首领显得如此突兀、局促、尴尬,所有的一切都一览无余。我低下头不忍直视,心里立刻产生一种悲愤,像是被人强扭着剃光了头,又像是相处多年的好友失联。
建筑是视觉更是环境的产物,剔除、剥离这自然的生灵,随意打破这二者内在的默契、和谐,人们已没有了敬畏之心,怜悯之情,无所顾忌地掠夺,恣意妄为地胡闹。
树是每个城市的穴位。树目睹着同类被一棵棵连根拔起,它们会不会在日益恶虏的生存环境中集体释放一种有害物质或是气体,来对抗人类的冷漠与不公。这个星球会不会终有一天被沙尘暴、雾霾吞噬?假如有一天我们终将被迫迁徙到另一个星球,那里还有没有我们最初赖以生存的树作伴?
我不敢再想。
树守住的是一城人的风水,倾听的是一城人的故事,目睹的是一城人的兴衰。愿它永远守候在我们身旁,一代又一代,绵绵不绝。

【作者简介】
贾浅浅,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作品散见于《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出版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获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诗歌奖等荣誉,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