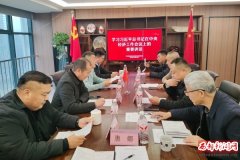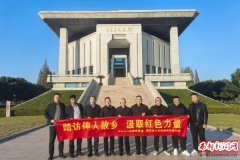作者郑媛近照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儿女老爱给我拍照片,什么留纪念,我心里明镜儿一样,不就是防着我走丢了寻人启事上好登嘛。”
老叔顿了一下咂咂嘴“不至于我跟你讲还真不至于。”
“我还就守着我家小琛不走了还就。”小琛是谁?可不是老叔的乖孙儿,当初把那胖小子生出来可费了姥姥家力气了,头圆身子壮实,跟养胎养的好有大关系,怀着孕大鱼大肉烧鸡羊腿燕窝都源源不断的补着,生这娃儿的时候老叔也在,手术室里面儿媳疼的直叫,他听着声儿一拍大腿,“这娃儿名字里得加个苇字儿”性急者叫佩苇,性缓者叫佩弦,老爷子是急了希望孙儿性子急点儿麻溜溜的出来,哦对忘讲了,咱这位老叔姓杨。

从那以后老叔就多了个掌上名鱼,名儿也敞亮,叫小琛,意思就是珍宝。
老叔这日子也是摸鱼过去了,偶尔跟隔壁王老大爷打打牌,自从这王老大爷花重金购进一只红毛鹦鹉之后跑得就更勤了些,逗鸟遛鱼一样没落,那叫一个自在,只是老叔发现一事儿很奇怪,老王每次打牌都要去好几趟厕所,时间还不短,老叔尾随几次后终于发现端倪,这老王屙尿始终不得章法,往往使劲挤才能挤出几滴来,实在没得尿了老王就抖吧抖吧收起来,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真真让人发笑。
老王说起这症结来“就总想尿,又不怎么尿的出来。”完活了收起来提溜着裤子感觉马眼一松,一滴两滴的就滑了出来,好在内裤是纯棉吸的很干净脱下来看也一点儿痕迹没有,但也就坏在是纯棉的,老王一脸嫌弃“自己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知道上面有,有就是有。”老王不容易。
老叔今儿来得巧,正赶上饭点儿,鱼腥草是老王媳妇儿最近常做的一道小菜,老叔年纪大了眼花没看清,箸着筷子夹了一筷,刚进嘴就觉着不对,老王适时来了句“老家伙会吃啊,这鱼腥草,利尿消肿,好东西。”老叔吐也不是咽也不是,在老王媳妇儿的注视下嚼吧嚼吧吞了,一张老脸皱成苦瓜,老叔不容易。
要说这老王自个儿也是高知人士,日本留学人送——‘臭弹专家’,一个屁十几个弯儿,晚上肠道不好更积一天的气儿都放了出来,噗噗噗一排炮仗,一放一个抽,老王一放屁,老王媳妇儿跟安了个屁感雷达一样,身子猛的一弹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直愣愣的瞪着天花板,在屁声里等待第二次困意,老王媳妇儿不容易。
老叔本来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搁这儿烂了,在这天井式大杂院儿里,养养鱼逗逗鸟眼一睁一闭也就算活过一趟了,何曾想到自己会过上与之前大不相同的生活,大杂院儿被开发商征收了,老叔儿子要走大部分安置费买了学区房,而老叔被安置进了新家——大茬儿爱心小筑,从此天高皇帝远,大家伙儿各过各的,逢年过节打个照面儿接去住个几天,也就算全了孝道了。
大茬儿路有个菜市场,老年人最佳聚会地儿,老叔有天路过,瞧见一圈儿人把什么东西围的严严实实,跑过去从人墙的缝隙里梗着脖子看,嘿,三只卷毛猴子蹲地上,按大小依次排开,活像一副不规整的劣等俄罗斯套娃,脖儿上还套个环儿,足有手指粗(三米长足有手指粗的麻绳)的麻绳三米长用来限制猴儿的活动范围,周围是挎着菜篮的大妈,扔根儿葱表演个绝活,围观的大老爷们儿小媳妇儿不停咂(嘬)嘴,啧啧的逗猴,有小毛孩儿好奇又不敢靠近离得老远扔去零食,猴儿够不着急得绕绳儿直打转,老叔瞧着有种物伤其类的感觉。
老叔祖辈务农,到他这代才出俩文化人,八斤宝似的养着,买房提车娶媳妇儿。小时候学校一放暑假就顶着大太阳给人帮忙在玉米地里拾土豆,地是一行土豆一行玉米的往下种,晒的晕了两眼一黑一屁股坐断人家两根玉米,完了赶紧爬起来悄悄扶好。
帮人拾完土豆当然免不了点儿‘好处’,走的时候搽着嘴边儿烧土豆残渣捧着肚子扶着腰一路走一路响屁。老叔记的老清楚了,小时候一周几毛的零用钱攒起来跑去小卖部买个泡泡糖,那时候‘比巴卜’就顶了天了,找个没人的地儿,小心翼翼拆开闻闻完了舔舔嚼吧嚼吧吐出来用纸原封不动的裹住,这样循环往复,就这破口香糖也能嚼个个把周,“现在比巴卜算个屁啊,市场都给各种外来货占了。”老叔咂咂嘴。
扯远喽,咱扯回大茬儿爱心小筑,老叔在这儿认识一人,刘大头。要说这刘大头当年也是镇上响当当的鸡头人物,白手起家盘下了小厂,经营不错,也算志得意满。大学生儿子趁着年节被吆喝回来想在镇上给相个媳妇儿,賊的不行折腾半晌,就为了赶着拆迁(前)凑个人头好多分两套房,倒也熟门熟户的,镇上哪哪家人好哪哪家关系简单哪哪家肯下苦都摸的门清儿,“反正迟结早结都是结嘛”刘大头坐在副驾驶上两脚蹬掉鞋子往前挡风上一搭端的是一副志气昂扬。
第一步是和前妻复婚,然后就开始着手儿子的婚姻大事,这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女孩儿在北京打工,一个月赚四五千勉强够开销,“搁外面漂着有啥意思,跟我儿结了婚了回来帮咱自家管管厂子才是个正经事儿。”
完了去年中风现在半偏瘫只能轮椅上过活,“哎呦喂拼死拼活赚那么多钱有啥子用哦,全填儿子窟窿了”邻街碎嘴婆娘压着嗓子絮叨,“到头来身边儿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老刘可怜哩。”
大茬院儿休息室有台公用投影仪,算是个消遣玩意儿,老叔对此嗤之以鼻,“嘿,这人一天到晚都被个机器消遣喽。”一直到天擦黑都有人耗旁边儿围着看,老叔不愿与院儿里人‘同流合污’,自顾自梗直背捶着老腰踱着步子晃荡到前厅取了当天的报纸回窝儿看去了。
有天中午院儿里的年轻小伙子,女护理员们凑一堆儿看得起劲,女孩儿们不时小声尖叫、嬉笑,闹哄哄的,老叔瞟了一眼瞧见俩金发碧眼的男人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戳了戳死盯着看的专心姑娘“这老外咋喜欢大男人?”眼线勾的恨不得飞进鬓角的女护理员嗑着瓜子抬头瞟了眼老叔“叔,你也来看嘛,反正闲着,打发时间呗,还蛮好看的。”老叔撇撇嘴端着茶缸走出去,“谁消遣谁呢这是。”
出了休息室拐个弯儿顺着一排紫树藤架子就能看着一方小池以及冒尖儿的池上亭,一溜儿的矮灌木过去又是俩池子,一池红鲤鱼一池王八,瓦上飞着鸽,池里沉着鳖,说来这大茬院儿也是个养老的好地方,老叔最爱的就是那几尾红鲤,每回都拎着一小袋吃剩的饼干碎渣来投喂,被护理员们发现好几次,嚷着会把鱼撑死不让喂,还是死性不改偷着喂鱼,“鱼有脑子的,饿了就吃,饱了就停,人家自有一套。”
老叔不服气,其实说白了老叔就是想小琛了,小琛在老叔安家大茬院儿之前就挂掉了,死状惨烈,凶手是小苇,先前提过老叔的乖孙儿。
乖孙儿拿小网兜去兜鱼玩儿,一张肉脸上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小圆脑袋晃晃,小琛就在他的小手中一上一下的扑腾,感觉仿佛行使着造物主的权利,一不留神呲溜一下小琛从他手里滑到地上,躺着扑腾。
小苇嘻嘻笑着拾了根儿牙签弯腰戳小琛,一戳一动弹一戳一动弹玩儿的起劲儿。过了会儿小琛不动弹了,小苇直起腰又戳了一下下手重了戳到眼睛,小琛的一只眼球被戳了出来,滚了两圈儿不动了。老叔回来了看着小琛一只血淋淋的眼睛气的直发抖,狠狠心黑着脸训了孙儿一顿,把个小娃吓的哇哇大哭直往妈妈怀里钻,看着儿子胖乎乎小脸儿上的泪痕,儿媳就更坚定了要让老叔在大茬院儿安家的心。
说起来大茬院儿里有俩出了名的臭棋篓子,老叔名列其中,老叔爱下棋,一手棋下的稀烂,老头又倔,难免与人发生口角,吵吵着“我先走我先走”一看局势不对“哎不行我不放这儿了”抽手就要把子儿取回来,眼看要输“你让我想想呗我这儿还有招呢”死乞白赖最后还是个输,偏生兴致还高的不得了。
这另一位,就当属老赵了,这老赵老了老了不服老⭐,眼瞧着要输,就开始偷子儿换子儿,面皮又薄,人一揭穿一张老脸臊的青红交错精彩极了。
真真俩老宝贝,院儿里人都不乐意跟这俩下棋,这俩臭棋篓子只能将就着搭伙儿下,也算自得其乐。
老叔小来可就穿过彩色衣裳,逢年过节都不一定有,一年到头也就次吧的好事儿,通常都是谁谁家结婚了谁谁家小娃入学了才会搞上一套新衣裳,布料是邻村大染缸出来的,几捆扎染好的粗布,家家户户拿着一年到头仔细着攒下的布票去扯,你家几米我家几米,谁家小子又蹿个儿头了,谁家姑娘成大姑娘了,还别说这扯布人心里可清楚的很呢。
老叔那时刚穿新衣,喜的不得了,在学堂里课间休息时一改往日坐座位上半步不挪抬不起屁股的样子,翘着个小下巴四处晃荡,下了学,刚巧遇着下雨天给浇个湿透,找个屋檐一躲,嘿,乐了,没下过水的新布掉了一身的色。等雨小点儿,红胳膊绿屁股的回家了,回了家了又是一番乐,爹妈指着老叔笑得不行,弟弟妹妹哄闹着来比谁的屁股颜色好看,哥哥姐姐边笑边扯了毛巾包住老叔脑袋。
到老叔儿子的时候,也穿过扎染粗布做的彩色衣服,儿子跟老叔一个德行,雨天淋了一身湿,回家兴高采烈炫耀自己的蓝胳膊黑屁股,老叔和媳妇儿也笑着,媳妇儿边笑眼泪边掉。
老人总爱讲些神神鬼鬼的东西,老叔不一样,这老小子可是个实打实的唯物主义者,牛鬼蛇神的他都不信,十八佛像弹个脑嘣权当打了招呼了,五方佛下点点头四处望望也算来过了。往年儿子儿媳赶正月里去上个香寺庙里拜拜,老叔看不过眼,“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法倒是一套套的。”
赶上有年儿子查出胃癌,老叔才慌了神了,一趟趟的跑前跑后,联系医院,询问病情,转账取款,一夜之间人仿佛老了一大截。儿子病情每况愈下,老叔悄不声响的跑去庙里,想着临时抱个佛脚⭐,买了最贵的香和莲花灯,抱着一堆东西,跨过鸟居,三步两步蹿到大殿门口,结果被人抢了先。
殿门口那儿趴着一个老妇人,涕泗横流脸上脏兮兮,行着五体投地的大礼,额头不要钱似的往地上砸,嘴里嚷着“佛祖啊菩萨啊,求求你救救我儿”声嘶力竭形状凄厉,端的是个搀不起拉不住的势头,老叔怔怔的看着,猛的扭头照原路折了回去。
老叔儿子那时刚工作,年轻气盛,脾气直性子硬一股子傲气恨不得实体化,觉着自己能力强啥都高人一着,日常从心里斜眼看人,搁天花板上走脚不沾尘。
说来也是象牙塔里长大的人,突然就被扔进社会这大染缸,一下回子喝了不少脏水,吐也不是咽也不是,哽到喉咙里还烧的心慌。被穿小鞋,被打小报告,被恶意指派,那士气是以看得见的速度萎下去的,老叔甚至能听见小火柴扔到冰桶里那‘嗤’(呲)的一声。话少了,笑脸少了,闷声不响日日烦躁不堪一点就着,做啥都懒懒散散得过且过一副破罐破摔的且行且乐样儿,整的老叔媳妇儿每晚睁着眼睛睡觉,老叔倒一切如常。
老叔媳妇儿撺掇着老叔跟儿子好好聊聊,排解排解,说是怕儿得了那个啥最近可流行的‘忧郁症’,老叔白媳妇儿一眼“噫,那么大一人,上吊的话,可能还真像沙袋。”
爷俩到底还是进行了一次谈话,大致内容是老叔问儿子早上吃的啥下午吃的啥晚上打算吃啥,算的上话的也就那么一句半句“人这东西也就靠一口气儿撑着,信念没了,气儿放了人可就塌了。”
老叔年龄一到,啥老年人常有的毛病都出来了,拉稀伴着便秘,苦不堪言,一个屁嘣出来几颗屎,星星点点不干不稀搁内裤里兜着,搞得老叔真真正正连屁都不敢放,有屁意了只能慢慢慢慢的挤出来,臀部收紧,肛门周围的括约肌用力控制住气流大小,不能太大也不能憋回去,憋回去这屁可就一去不复返了,慢慢的排出气体,完了舒一口气,背上已是一层薄薄冷汗。
到这个年纪,胯肌失了效控制不住自己,身体不听指挥,便秘是最痛苦的,肛门不完全失禁。吃辣了拉屎时肛门口周围火烧燎过的疼,吃太凉性止不住的拉稀兑水似的小米粥往外喷,搞得老叔好久不吃小米粥,身体仿佛被开了个口子,坏掉了似的哗啦啦往外流东西。
有时看着院儿里中风的老人被插上导尿管儿,穿着纸尿裤,一天三次的往外端排泄物,换洗、擦身,老叔觉着人要像这样活着可真没意思,屎尿都得供人瞻仰,只剩下隐私被摊开示众后带着羞窘的麻木,这滋味儿,可想而知。“不想气味难闻的活着,可真难。”
老叔觉着自己跟儿子可能是属性不和,从小到大没一件事儿是顺溜达成一致的,在对婚姻的态度和结婚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讨论的俩人直冒火,论到最后吹胡子瞪眼不欢而散还没谈出个所以然“婚姻又不是到年龄要完成的任务”儿子撂下这句话摔门而去,老叔抱着脑袋说不出话来,半晌喃喃道‘还是太年轻了终归幼稚’。
老叔摸着无名指那儿一圈儿戒痕,生活好了之后跟老婆一起订做的戒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仪式感,老叔不懂,可这一戴也就几十年,晨起洗脸摘下来搁洗漱台子上,麻溜整完又给套上,几十年来已经成了个一天打头的既定动作,今儿早上给整丢了,咋都找不着,急的老叔直跺脚。
老叔摩挲着戒痕,不浅一圈儿槽,这些年来老叔胖了又瘦了,来来回回手指粗不少,刚开始戴上还能悠哉转动,后来就紧箍着,跟这段婚姻的感觉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个人儿跟那儿给念紧箍咒似的紧绷。
老叔那年代,到年龄不结婚是会被诟病的,闲话见缝插针往你父母耳朵边儿上凑,巴掌大的地儿生活乏味每日麻木重复,一星半点儿八卦能传的飞了天了,恨不得给你安上六胳膊仨脑袋才肯罢休,老叔回想起来只觉得一片混沌。
后来儿子到底结了婚,老叔也算松了口气,这混小子总算是成家了。婚礼办的气派,恨不得把沾亲带故的人都招来沾沾喜气儿,老叔私底下悄悄问过儿子爱那姑娘么,做老子的到底是希望那稀少幸福的可能性落到自家儿子身上,老叔儿子笑笑“怎么不爱”,爱这东西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刚刚好一小勺,不多不少不黏着不疏远,调剂生活倒也来的舒服,算不上消极,顶多是透彻惹人难过罢了。
电视里放着在裸滨鼠基因里找到了长寿方法,老鼠蹦跶三十年换算成人类寿数那也得有个六百年,老叔啧啧感叹,“一百年都活不好活六百年那可真真煎熬”。
要说这时间长短可真没个界定,老叔最开始还坐过人力拉车,后来是小三轮儿,远的地方就搭绿皮火车,从几毛一位涨到五六块几十块,老叔讲起来觉着吓人,“不大不小一长条铁盒儿,里面塞那么多人”大包小包往上扛,热闹蒸腾,活像什么饥饿的怪物口袋。
众生百态都在这小小方寸之地展现的淋漓,各种声音烩成一锅。老大爷一口老痰卡嗓子眼儿咳嗽半天不上不下出不来憋的从脸到脖子红成一片儿,裤腿沾满石灰的中年男人靠着车壁一阵儿紧跟一阵儿的打鼾脑袋随着列车晃动一下下往玻璃上敲还照睡不误,双肩包背在胸前的学生样小青年打了开水吸溜起桶面差不多了摸出包边儿塞着的香肠撕开吃了完了又把泡面汤给喝的干干净净,戴着全框黑边儿眼镜的女人拿着张纸不时抬一下镜框擦一下眼睛擦完了翻个面儿折一次擤起了鼻涕,年轻小夫妻为着莫名其妙的暧昧短信你一句我一句开始争执,围着肚兜被放在小桌板上坐着的三四岁小孩边咧着嘴嚎边迷糊着打瞌睡头一下下的点着,点醒了接着扯开嗓子嚎。
车上通常没座位可坐,直愣愣站几个小时学聪明了抄张报纸往地上一铺,后来有样儿学样儿大家都这么整,台阶过道甚至厕所门口都坐满了人,抬脚落脚一声骂,整得跟跳芭蕾一样,踮着脚尖儿跟着过隧道时明明灭灭的光线蹦,好不容易坐下来一个屁嘣脸上,甚至能分辨出人吃了韭菜盒子,整块儿空气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大茬院儿附近来了新住户,废品站被这人接管了,四十出头的男人长一张尖嘴猴腮三角内裤似的脸,颧骨突出腮帮子瘪俩眼角肉往下耷拉着,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给薄薄一片儿下唇托住唇线模糊,上面俩悬壶的鼻孔朝天露着,眼睛细长单眼皮儿肿眼泡一不留神就成了吊梢眼。
刚开始周围住户都很警醒,看着不像好人的单身中年男人住在简易板房里,早出晚归,大家都暗地八卦起来睁大眼睛等着有事发生呢,没想到那收废品的男人就那么安安稳稳本本分分住下来了⭐(太刻意),还有人看着他喂流浪猫,有人去卖废品的时候搭上过话,长的一副阴沉相说起话来倒是出人意料的谦和有礼。
老叔也知道这人“人是个好人,就是长一副薄福薄命相”摇摇头,“啧啧,这年头脸给整成第一消费品了”,先入为主的决定你的品性,家庭,背景,以至于人总容易被看到的东西欺骗。❗❗❗
老叔乖孙儿被人打了,嘿,老叔听到这消息那个气啊,儿子老来得子平时磕着碰着都心疼要死的宝贝疙瘩给人揍了,那能不光火么。
论起来为啥和人打架还被打了,那得说说下午小胖墩儿跟班里同学约好下课厕所见,正发育的大男孩儿憋着劲儿要比谁尿的远,俩货绷着背往池子里尿,汁液飞溅,老叔孙儿可能是下午放过水料不多了,渐渐力不从心起来眼瞧着要输胡乱瞟了眼隔壁对手的小弟弟,没憋住噗嗤笑了,白白嫩嫩小小坚挺的精致金针菇,隔壁男孩儿顺着老叔孙儿的眼神脸蹭的涨红了,老叔孙儿飘着呢还没回过神来,人的拳头就在脸上了。
膘肥体厚的战五渣⭐胖小伙儿顶一乌青眼眶,下巴还给挠破皮蔫了吧唧的回到家整了俩鸡蛋滚滚又找冰袋敷敷捯饬老半天,小胖墩儿被妈妈温声安慰着,来了劲儿了眼圈儿一红,掉起泪来,哭的那是一个鼻涕一个泡,老叔瞧着这不争气的哭包样儿气不顺的厉害。
老叔听完哭笑不得“嘿,这打可不是白挨的”。
老叔有心理洁癖,路上碰着人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老叔都要咧远远儿的,生怕什么莫名其妙的沫子喷到飚到自己,“别瞧着看不着,那可是实打实的病菌”。
邻居家一小孩儿睡着了妈妈要去买东西家里没人请老叔给看着会儿,小家伙长的稀罕软软糯糯一团老叔接过来抱着不愿撒手,过了会儿可能睡饱了饿了张嘴嚎起来鼻涕眼泪齐流,又湿哒哒尿了老叔一手,小脸儿上挂着泪一溜儿黄鼻眼瞧就要流进嘴里,老叔挠心挠肺跟抱着个烫手山芋似的分分钟想给撇地上撒手不管,前一阵儿还是白白胖胖的心肝宝贝,这会儿子成了恨不得拍地上的病菌疙瘩。
好容易等小家伙老妈来抱走了,冲进卫生间逮着那手就狠劲儿搓,搓的都秃噜皮了才罢休。
周围高中组织来敬老院看望老人,做社区活动要加分的听说,大茬院儿也在其中,说是来陪着聊天下棋读报纸。
中午时分一群穿橙马甲的半大小伙儿姑娘拥进院里,新奇的四处张望,俩学生非要搀一行动不便老大爷上厕所去,偏偏又不得要领,一拖一拽把个胳膊可使劲儿揪,一行三人趔趔趄趄,大爷被左右架住上不是下不是散架了都,剩下的老人也都被招呼出来,坐太阳坡里晒太阳,一牙差不多掉光的瘪嘴干瘦老头伸脖子朝门口望望眼睛在这群橙马甲手上打了个转儿“来嘛咋不带点儿水果啊奶啊啥的”。日头渐高又涌进一波穿绿马甲的,老叔算是看明白了“期末了嘛赶时间哦”。
老叔抱着个苹果啃,瞧着热闹心里直犯嘀咕“这还形式主义的很”。
小李一标准怂人,喜欢的姑娘结婚那天吃了20个烤串儿打着饱嗝喊着哎呦厕所里蹲着,
老叔可讨厌夏天,坐久了闷一屁股汗,半干不湿的黏屁股蛋子上,捂出一屁股痱子,红疙瘩一片儿片儿钻心的痒,挠一点儿成片儿的痒起来,痒得狠了逼急了拿指甲尖尖小心的挠,挠完舒服的出一口气。
成日里燥热不堪,铺竹席面儿上的槽把肉给硌出印儿来,一不留神深深浅浅爬一脸,大半天才见消,人碰着了都笑笑问声“老杨中午睡的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