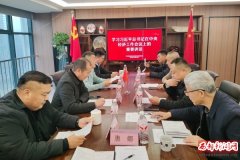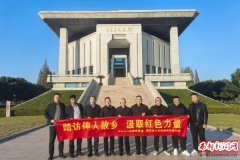陈忠实,1942年生,陕西西安人。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党组成员。自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告别白鸽》、《家之脉》、《原下的日子》等著作76种,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等各类文学奖21项,多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国文字出版。代表作《白鹿原》迄今已发行逾20 0万册,在国内外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文学界有较高评价。
2009年度陕西“最具文化影响力人物”评选中,关于陈忠实是这样介绍的:“2009年,又是他的一个丰收年。历时两年写作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读者、专家反响热烈。为全国各地作者撰写20多篇著作序言,扶持青年,奖掖后进。参加‘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西安颁奖会,与多所高校学生座谈创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陈忠实过去一年中创作、工作、生活之一斑。事实上,陈忠实一年中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以及工作和生活远比这个介绍要丰富得多。我知道的他,是每天都忙着,从早到晚,几乎没有节假日。我常常慨叹,陈忠实的身上有太多儒家的入世进取精神和道德自律人格,太多宋儒张载以来关学思想的务实人生态度,甚至太多从祖辈从骨子里带来的农民的刻苦勤劳,而太少甚至没有道家的逍遥思想和人格,一年到头忙着,为了社会责任,为了做人的义务,严于律己,不让自己消停。
1 50岁以前,陈忠实一直生活、学习、工作于灞桥农村。可以说,他是一个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他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名为《乡村》。
1942年,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南坡的西蒋村。这是一个小村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父亲陈广禄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会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这在当时的农村,就算是有些文化的人了。父亲对陈忠实的要求很实际,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要我念点书,识几个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他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一碗饱饭,我一生的年华岂不虚度了?”
陈忠实的文学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赵树理。读初二时,他在文学课本中读到赵树理的一篇小说《田寡妇看瓜》,这篇小说给陈忠实的生命注入了文学因子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学了这篇课文,陈忠实十分惊奇:这些农村里日常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进文章?他暗自思量,这样的人和事,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我也能写这种小说。“我也能写这种小说”的念头由此在他心里萌生。此后,他借阅了当时能看到的不少赵树理的作品。第二个人是刘绍棠。刘绍棠使他对文学的“天才”问题有所思考。陈忠实对文学发生兴趣时,“反右”正在进行。“神童”作家刘绍棠被定为“右派”,给陈忠实的印象最为深刻。少年陈忠实觉得“天才” 、“神童”比“右派”帽子更为神秘,因此对刘绍棠很感兴趣,又借阅了刘绍棠的不少作品。第三个人是柳青。他对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他前后买了丢了、丢了又买了9本《创业史》,这对他来说,“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一个数字”。由此可以想见柳青对陈忠实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早年的阅读塑造了陈忠实的文学理想,也塑造了他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所有这些最终凝结为一点,那就是乡村,生活的乡村和文学的乡村。五十岁以前,陈忠实一直生活、学习、工作于灞桥农村。 1982年7月,陈忠实结集出版的平生第一本书也是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就名为《乡村》。
1962年,陈忠实高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小学教师。此时的文学,对于陈忠实来说,既是安抚灵魂的良药,同时也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他一方面积极教学,努力当好小学教师,另一方面刻苦自学,读书,写作,观察生活,提升自己。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他的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发表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此后又发表了几篇散文作品。陈忠实原来的人生设想是,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大学自学完成,接着再不断发表作品,朝着改变命运的作家道路上迅跑。但是很快,他的作家梦就破灭了。“文革”开始,他在西安街头,看到自己崇仰的作家柳青被反绑着手沿街批斗。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柳青,也是平生仅见的一次。回家之后,他把自己几年来记了几厚本的日记和为创作做准备的生活纪事,拿到后院烧毁了。此后多年,陈忠实再也没有读过文学书。
1973年,陈忠实写下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并发表在当年创刊的《陕西文艺》第三期。此后,他每年写一个短篇,直到1978年。那一年初夏,陈忠实读到《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这是影响他“转折”的一次阅读。刘心武这个名字从未听说过,但这篇小说却让他深为震惊,用他的话说,是“心惊肉跳”, “小说敢这样写了!”他是在麦草地铺上躺着阅读的,读罢却在麦草地铺上躺不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在陈忠实看来,《班主任》的发表具有文学“解冻” 的意味。他意识到,一个时代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也应该重新调整。 1979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心中洋溢着强烈的创作欲望,连续写下十个短篇小说,这也是他业余创作历程中收获最丰的一年。
2 50万字的《白鹿原》,是陈忠实历时六年艰辛创作完成的,此后,他一直没有再写长篇。这不禁令人想起他著名的“蒸馍理论”:创作就像蒸馍一样,面要好,酵头要老,工夫要到,气要饱。蒸馍过程中,千万不敢揭锅盖,一揭就跑气了。
1982年11月,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城里给他分了房,但他人没有进城,依然住在乡下。当陈忠实的创作酝酿着重大突破时,关于拉美文学以及国内“寻根”文艺思潮的文学阅读,给他带来了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启迪。1985年,在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他萌生了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念头。这部长达50 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陈忠实历时六年艰辛创作完成的。据陈忠实说,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用了两年时间准备,用了四年时间写作。这就是说,陈忠实是在44岁时开始准备这部后来被其称为“死后垫棺做枕” 的作品,至50岁时才完成。陈忠实说,他写这部作品,共写了两稿,第一稿拉出一个大架子,写出主要情节走向和人物设置,第二稿是细致地写,是完成稿,精心塑造人物和结构情节,语言上仔细推敲。19 92年至1993年,《白鹿原》分两期刊载于《当代》杂志。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单行本。1997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确立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地位。问世17年来,《白鹿原》一直处于畅销和常销之中,被国家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 系列,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入选改革开放“30年 30本书”,并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目前正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
自《白鹿原》之后,陈忠实一直没有再写长篇小说。他还写不写?写什么?这是人们最关心的。甚至,还有人问,陈忠实还能写出高过《白鹿原》的作品吗?实际上,陈忠实迄今一直没有透露过他要写长篇小说的信息。有一年,陈忠实请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在白鹿原餐厅吃饭,我也去了。席间,我对陈忠实说,你最熟悉、体验最深的,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十年间的中国农村生活,也就是《白鹿原》完成之后的这数十年,你应该接下来再写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从而与《白鹿原》一起,构成关中农村也是中国农村真正的百年史,这将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李建军也赞同此说。陈忠实则沉吟不语。后来,我看到陈忠实买了一部卢跃刚写的《大国寡民》,这是一部写陕西关中一个有名的村子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变化的纪实性作品,这部书曾在几个朋友中间传阅,我也看了,我注意到陈忠实在读此书时写了不少眉批和札记。陈忠实还一再叮嘱,此书一定要还他,他要当资料保存。2009年,有一晚我和他闲谈,他说一直想写陕西户县的杨伟名事件,也就是有名的“一叶知秋”事件。陈忠实为此曾走访过许多人,积累了一些材料。他说原准备写一个10万字左右的中篇,但觉得写一个中篇可惜了这个题材。我说,十来万字或者再稍长一点,就是一个小长篇了。虽然不一定很长,但这个题材所包含的社会和人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陈忠实又一次沉吟不语。我不禁想起他的关于创作的“蒸馍理论”:创作就像蒸馍一样,面要好,酵头要老,工夫要到,气要饱。蒸馍过程中,千万不敢揭锅盖,一揭就跑气了。
3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业余作者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生过程,而在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上,陈忠实更是经历了许多次的“蜕变”,他是不断“破茧而出”逐渐蜕变过来的。
用陈忠实的话说,这个“破茧而出”的过程叫做“剥离”。对自己第一次“剥离”意识的发生,陈忠实有一个详细的叙述,显得意味深长。1982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受其供职的西安市灞桥区派遣,与另一个水利干部一起,“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30多个大小村子里,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分田到户”。有一天深夜,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莲池里铺天盖地的蛙鸣却宣示着春天。我突然想起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生活和历史中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令他惊诧,也不能不令他思索。陈忠实虽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但他对于农村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认识,却从少年时起就受到赵树理、柳青以及李准等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当初就是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感动,才决心走上文学之路的。而且,他后来近20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主要就是为人民公社体制服务。现在,时代变迁,人民公社消亡了,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变革。直到第二年,看到分给自家的地里打下来的麦子,竟有两千斤之多,算算全家尽吃白面就可以吃两年,比起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事实胜于雄辩,他心中一些困惑了很久的疙瘩才解开。这个“剥离”的过程生动而具体,也很说明问题,观念的转变不是说变就变的,它需要反思,也需要时间。作为一个必须具有思想者素质的作家,陈忠实显然对自己思想的某些“迟钝”或者说是“滞后” 有所警觉,从而认为自己从精神到心灵都很有必要经历一个自觉的“ 剥离”过程。
在陕西作家群陈忠实那一代作家之中,路遥与陈忠实一样,也是现实主义作家,他出道虽晚,但当时的创作成就却最为突出,对陈忠实造成的“压力”和“动力”也最大。陈忠实后来说,路遥的创作特别是《人生》的创作,对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甚至具有“摧毁与新生”的作用。1982年,当陈忠实一口气读完路遥发表于《收获》上的中篇小说《人生》时,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感觉———“是一种瘫软的感觉”,这不是由《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陈忠实很受震撼。此后连续几天,陈忠实一有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行或坐,反思着他的创作。《人生》中的高加林,在陈忠实所阅读过的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读了路遥的《人生》,他“惶恐”过,“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与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研究农村变革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由此而引发了我对自己创作思路的更为严峻的反省”。在乡间,陈忠实碰到一个青年,那个青年对他说,“你也是作家,你咋没有弄出个《人生》?”陈忠实说,这让他重新思考怎样写人。思考的结果是,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只有准确了才真实。这一年的冬天,陈忠实凭着在反思中所获得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他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该作品后来获得了《小说界》首届文学奖。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评论家李星一见到陈忠实就说,“你今年再不把长篇小说写完,就从楼上跳下去!”陈忠实自然感觉到了文学朋友在为他着急,但他心里想,急什么,不急,一定要弄好再说。这也促使他下决心把正在创作的《白鹿原》打磨得更精到。
4 陈忠实是一个从中国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踏过泥泞五十秋”,一个“踏过泥泞”概括了他几十年深刻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
在当今陕西乃至在全国的作家中,像陈忠实这样真正经历过底层生活并经历过苦难的作家,恐怕不是很多的。这样的经历给陈忠实的性格打下的烙印,自然是复杂而丰富的。陈忠实身上既有关中血性汉子那汹涌的不可遏止的激情,同时也有铁桶般的禁锢和巨石在顶的沉重压抑;既有多年做领导工作的谨慎与周密,同时也有文人的旷达和狂放;既有彬彬有礼的谦和,也有崚嶒的傲骨。
陈忠实是个足球迷,而且是个超级球迷。有一年7月,正是世界杯赛如火如荼的日子,西安有一家书法俱乐部想请陈忠实写字。老陈说,写字行,但不能误了看球赛。对方就安排在了渭河边草滩镇的渭水园度假村,那里有农家小院,厅堂里有大彩电,也很安静。后半夜的时候,老陈乘着酒兴,给同来的我讲起了他早年经历的一件事。他说,那时他还在灞桥乡村里教小学,小学分东西两片,他是东片的教研组长。一天中午,派出所来人把西片的教研组长抓走了,说是因为那人破坏军婚。陈忠实说,那时犯这样一个错误,一个人一辈子就全完了。后来他去给那个人送铺盖,一路上感慨万千。那时他已经搞起了业余文学创作,他想,如果这一生还要干点事,弄出点名堂,就绝不能在这样的事情上栽倒。陈忠实说,这件事一直在心里埋着,自己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始终没有写。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写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其中《日子》和《李十三推磨》反响强烈,收入多种选集,多次获奖,但他写得更多的是散文和随笔。他的很多散文都是回忆往事的,从上学路上鞋底磨穿脚部血流不止,到因家贫辍学老师流出惋惜的眼泪,一直写到一棵小树,那些曾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迹的事情,差不多都被他写到了。我想,他之所以还没有写这件往事,也许因为有某些不好把控之处吧。从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我对陈忠实及他们这一代人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陈忠实这些年来也去了不少地方,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还去了台湾。走出白鹿原之后,陈忠实的视野无疑是更开阔了,而有了这辽远视野的参照,再回眸他的白鹿原,回眸关中这块土地,他也许有更多更新的体悟。他的游历,也许正是拉开距离的一种寻找。近年来,他则更愿意沉静下来,居于城中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不是隐,他的思想中,没有隐的意识),读书,思考,写作。我们祝福他!(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