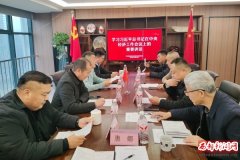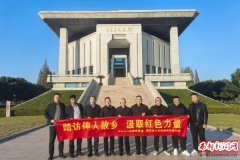陈维礼,坚守汉唐黄土和树根的人
文/图 火炎
西安深秋的阳光,通透中泛着金黄,把万物都照耀成发黄的老照片的感觉,令人莫名地失落和怅惘。
我从南方叶落归根般地赶回了西安,个中因素也是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多沐浴些与南方不同的阳光。西安是我人生经历中极为重要的记忆之一。
西安城的变化已使得我很难找到许多儿时的痕迹了,唯有令我怀念和留恋的是阳光的色彩,依旧没变。我遐想,远古的阳光在这个季节里是否也是这般色彩?倘若如此,那我岂不可以随着这阳光,让思绪穿越到远古?
“阳光是不是远古的,我不敢说,但这乐游原上的黄土和树根肯定是,起码也是汉唐时期的。”陈维礼抓起一把崖边上的黄土对我说到。

陈维礼抓起一把崖边上的黄土说道,乐游原上的黄土和树根应该是汉唐时期的。
原,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 四周陡峭,顶上平坦。此类地貌,关中多见。
广为人知的概念,大多都是从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获得的。
其实,乐游原的渊源更为久远。
“乐游原兴于汉代,叫乐游苑,后盛于唐代,才叫成了乐游原。这里文脉兴盛,承载着深厚的文人诗话、园林、宗教等历史文化。”陈维礼用一口纯正的西安话说道。
“说起乐游原这地方,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塬。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诞生在这个原上。我曾统计过,《全唐诗》、《全宋词》中题咏乐游原或与乐游原有关的诗词总共有八十多首。”陈维礼说。

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唐长安京城人游玩的好去处。
乐游原,作为园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秦代的乐游原属于上林苑的一部分,是王公贵族游猎的地方。秦穆公时上林苑被分为五苑,宜春苑是其中之一,乐游原属于宜春苑的一部分。西汉时,始有乐游苑之名。《汉书•宣帝纪》记载:“神爵三年,起乐游苑”。 神爵三年为公元前 59 年,因此,乐游苑之名距今已有2077年的历史。
唐代长安城中公共园林里最著名的是乐游原与曲江池。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乐游原上建造亭阁。唐景龙三年,中宗李显在一年中,两次游幸乐游原上的太平公主山庄。唐玄宗时将这里先后赐给了宁王、申王、岐王、薛王做住所,经过四王的扩建后,乐游原景观更加幽静别致,逐渐成为长安城居民登高游览的聚集之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唐长安京城人游玩的好去处。
乐游原南坡下,有个观音庙村,陈维礼就生长在这个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
“我对乐游原的依恋完全出于一种情怀,而且是随着年龄与日俱增。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听老人们演绎着乐游原上曾经发生的爱恨情仇故事外,还因原上清静宽广,是我们当年背书玩耍的好地方。尤其是夏天,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电风扇。晚饭后,男娃们卷起个席子约上两三个胆子大的小伙伴到原上纳凉聊天成了儿时的一大乐事。
乐游原的沟底下是村上的坟地,白天也就罢了,到了晚上,再大的胆子独自一人是绝不敢上原的。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晚上,我和表兄弟三人相约卷席到原上纳凉。席地闲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凉风吹醒的我,发现他俩不知什么时候都下原了,顿时吓得魂飞胆破,席子都顾不上拿,连滚带爬地下了原。第二天,我挨个上门把他们美美地教训了一顿。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都瘆得慌。
在乐游原周边生活的人大多都认识陈维礼,而且在当时西安的企业界还是颇有名气的。
陈维礼有些传奇:当过武术教练,办过合资企业,北大研修过,还在大学讲过课,年轻的时候不仅当选为省政协委员,还成了黄埔生的快婿。
陈维礼很怀旧,说起往事,滔滔不绝。他有一种让周围的人跟他一起往过去走的本事。无论是说话神态,还是提及往事,都会把你带入到事件发生的那个时空中,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消失的失落和悲哀。
无论怎样辉煌抑或暗淡过,只要说起乐游原,陈维礼顿时就会一脸惆怅,不由自主地叹息道:“如今生活在商品社会的人们都疯咧,总是把眼光盯住这块老祖宗的遗产上,做着自己的发财梦。生生把乐游原折腾成了个‘乐游岛’。”
从执着地要把乐游原的原址保留下来这事上,看出陈唯礼身上那股关中汉子的倔劲儿。他就是要给后人们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历史。
交谈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自打离开学校后就忙于生计,有二十多年都没空儿到原上看看。那还是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独自到原上散步。走到原上才发现乐游原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不仅有了养猪场,更有甚者还挖土卖钱,把将近五公里长的乐游原割裂的只剩下不到一公里了,我内心很是难过。” 他被眼前看到的这一切震惊了,心被刺痛了。回到家,他立即起草了抢救保护乐游原的提案递交到省政协。出乎意料,提案很快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干预。乐游原从此得到了保护,养猪场被清理,采挖原土被禁止。说到这儿,陈维礼诙谐地模仿着村里“大舌头”当时说话的语气:“人哪政府下令咧,不叫咱再挖原上滴崖土咧,再挖就是犯法。”
尽管如此,陈维礼不敢再松懈了。他放下手边的事情,拿出资金,打算用文化来保护乐游原。经过他几年的艰苦努力,植树绿化,立石树碑,把个乐游原修整的井井有条,郁郁葱葱,还在原上创建了“岂之人文讲堂”。一时间,讲堂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张岂之、雷抒雁、陈忠实、贾平凹、熊召政、吴克敬、舒婷、孙皓晖、陶艺等一批著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他们相聚讲堂,谈古论今,写诗作赋,各显神通。就连远在美国的国学大师、文学博士罗锦堂老先生也为了表达对陈维礼重振乐游原所做的贡献,给原上新成立的“刘少椿古琴艺术馆”寄来了亲笔题字。

陈维礼在乐游原上创建了的“岂之人文讲堂”。
陈维礼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属于自己的认知。”
东方文化的确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像陈维礼这样敢做敢当的人,只能借助文化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保住乐游原。他选择了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把自己和一块历史悠久而神奇,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西安就如同一个饱藏历史文化的宝库,不要说打开闸门,就是露出一道缝隙,历史文化就有可能涌将出来。
陈维礼说,“不仅这黄土是秦汉唐的,这树、这根都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就连咱这语言少不了也是秦汉唐的。”我说,还有这阳光。
斜阳下,陈维礼站在乐游原的一个制高点上,语气坚定地说,“不能再让挖了,整个乐游原从东到西就剩下长不到八百米,南北宽不到三百米的范围了。”他的这番话,使我联想起当年电影《上甘岭》中,七连孟指导员将阵地交给前来增援的八连张连长时说的那段话:“上甘岭地面不大,东西长只有五百公尺,南北宽不到三百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地交给你了......。”眼下的陈维礼却是一个人的坚守,无望地等待着支援。

陈维礼在乐游原上创建了的“岂之人文讲堂”。
那天晚上,我们聊的十分尽兴,只要讲到如何守住乐游原,陈维礼就显得特别激动。他说:“现在是个大好的时机,进入新时代,国家大力提倡恢复和传承传统文化。那么如果连历史遗迹都不重视,不加以保护,那传统文化岂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西安的大小雁塔是唐代留存下来的仅有的建筑物,但那是人文建筑,乐游原可就不一样了,它是自然加人文的双重产物,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毫无疑问,陈唯礼是乐游原上坚定的守原人,他要坚守的不仅仅是这些,更深的理解是在坚守一个民族历史的黄土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