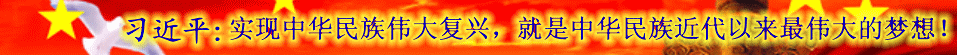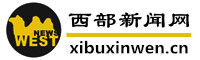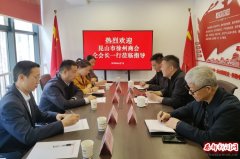老诗人胡征印象
肖云儒
老一代著名诗人胡征,一生诗作不多,却在中国现代诗坛留下了自己的足音。以其诗读其人,我想说,他是一位有独创性的诗人,一位有自己诗美追求的诗人,一位有生命大痛苦而超越了生命痛苦的诗人。
他用诗预告,自己的一生
我不愿在这里复述胡征漫长而坎坷的一生,倒想蒸发掉具体的人生经历、径直来看看诗人六十多年创作生命中的心灵历程。恰好有一首诗对这一精神历程作了极好的象征性表述。这首叫《初试》的诗,写于1941年,是他的早期作品,好象有什么神秘力量,预告了他一生的心迹。

1953年的胡征
这首诗描述了一位青年战士初次跨马飞奔的惊险经历。一开始是激越狂热的飞奔:跑啊/追赶大风/跑啊/追赶太阳/追赶骄傲的云/不让云的影子/超过我的头顶。
刚跨上马背的青年,精神上无羁无绊,内心充满了豪情壮志。后来,马跑得太快,这位初驭者开始萌生了恐惧,终至摔倒在大地上:空气的唿哨声/咬住我周身的神经/远处的山,近处的城/在我眼前翻滚/行路人惊奇地望着我/我的腿在颤栗/一只脚脱出了马蹬。
他发出一声惨烈的呻吟:这世界舍弃了我啊/眼前爆炸金花。
他浑身剧疼,但生命还在,精神没有倒。他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去追那正腾跃的骏马,决心不被马征服。于是,我们看到:
当我追上它/喘着气,抓住缰绳/准备给它一顿痛骂/但见它/不是我那年轻的马/而是一匹大骆驼/理想的金骆驼。

时代变了,烈马变成了金骆驼。骑手也变了,由准备发泄报复,到深情地礼赞已经变成了“金骆驼”的“马”。被命运惩罚的诗人,最后却超越了命运。这种超越,又受惠于时代和个人命运深沉的变化。
胡征一生的精神历程正是这样一个三部曲:青春的追索——中年的幻灭——晚秋的超越。
不幸而又万幸,这首诗一语成籖,竟然将诗人半个世纪命运和精神历程言中。
“独创是天才与庸才的分水岭”
“没有独创”,胡征说,“河都直线地流,鸟都直着着嗓子叫,花都按一种模型开放,世界就不成个世界。”当然也就更不象艺术。胡征的命运虽几经曲折,艺术上却始终坚持对独创性的追求。“独创,是天才与庸才的分水岭。”即便入户于“牛鬼蛇神”,他也决不当思想和艺术的庸才。
在文学史上,以诗歌吟育战争者不谓不多,但用长诗正面反映有数十万大军参加的战略决战者不多;而用抒情体长诗来写大战者,更是鲜见。《七月的战争》共十章二千六百行,《大进军》共四个篇章十七节二千五百行。两部史诗虽然将叙事和抒情相间杂、相溶汇,却以抒情为依托,以抒情从结构上、情绪上组接、贯连故事,又将叙事溶解于抒情之中。西部战争史诗都从战士的感觉来写战争,而不是从哲人的视点写战争,抒情主体与描绘客体同位同向同步,熔为一炉。不能说这种依托、贯连、溶汇已达天衣无缝、老到精致,在诗歌创作上却是带开拓性的创造。它为以抒情长诗正面写大战踏出了路子,开辟了天地。

“五四”以来,在中国新诗创作的长河中,浪淘尽万千风流人物,披沙拣金,出了多少好诗人和好的诗论家。然而,身兼诗人和诗论家二任于一身的人,在诗情与形象营构和诗论与哲思开掘上花开两朵的人,以诗事入著、以美文写哲思,以情象抒理象的人,确实凤毛麟角。艾青是一位,在他的诗集旁放着沉甸甸的《诗论》。胡征也算得一位,在他的诗集旁放着同样沉甸甸的《诗的美学》。
翻开此书,《诗问·代序》开宗明义一百六十三个关于诗歌创作的“天问”,犹如天籁回响、提壶灌顶,以充盈的真气震慑了读者。那天马行空,那博大精深,特别是命乖时背还坚执地上穷碧落下问黄泉的探究精神与思考胸襟,都不能不叫人想起楚国的那位行吟的先哲屈原。开篇如此,遑论其它。
“你的生命里,结晶着他的心灵”
先看他《石象》一诗的第二节——
古代的工人/劈开大山的岩石/用锐利的铁器/精细地雕出你的生命/于是你的生命里/闪着他生命的光辉/你那凝视世界的/圆睁着的眼睛/你那衣服上起伏的皱纹/都是他心灵的结晶/他是你形体的创造者/你是他庄严事业的旗帜。
这首有象征色彩的诗,无异于诗人关于艺术美的宣言,关于诗人和诗、美的创造者和美的关系的阐释。诗人呕心叨血雕出了诗句,使文字有了生命。于是诗的生命中,闪着诗人生命的光泽;诗的生命,无一不是诗人心灵的结晶。

作为一个以生命体验美的诗人,胡征毕其终生追求着自己的诗美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自身抒情气质的发掘、扬砺和调适,二是对中西诗歌传统的溶汇和创新。
诗是感情之雾的露珠。抒情气质应该是诗人的精神特质,就胡征来说,是他生命和艺术的底蕴。他以自己的抒情气质去感知世界,使情与象、情与理、我与世界相互交孕,产生出自己的宁馨儿。
在1940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圣地革命青年壮志豪情盈怀的那些年月,他却抒写了如此独特的感受:
我曾怀着稚子情思/踏着晚春的落月/将紫藤的花朵摘来/藏入枕边海滔的诗集……(《紫藤花》)
在《白衣女》中,他对“革命友谊”、“同志爱”的感受,也充满了诗人感情深处一绺柔鸣。
到了两部战争史诗,柔情被战火煎烤成烈焰,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战争中人的感情世界,仍然是对战争场面的感情把握和抒情表达。他所以采用抒情体、长诗来正面表现大战役,也许正是诗人特异的抒情气质决定的。是诗人的抒情气质选择了前人少有的路子,创造了诗美的新境界。
到了晚年,胡征的抒情气质又有了变化,变得洒脱,有时又尖刻,因而深刻。洒脱,如《碰杯》:
你古稀高寿/——少年的灵魂/我花甲青春/——童心未损/举起诗海碰杯/愿望建于最美的黎明。
这是花甲已过的诗人在历尽苦难复出之后,送别访华的美国哈利·莱文教授时写的,果然童心未泯,真情依旧。
洒脱当然不是消极避世,不是半睁着眼。在晚年平湖秋月般的抒情中,时时有尖利的浪花飞溅而起,如《鹿角椅》-诗,在见到清太宗坐过的鹿角椅上罩着虎皮,他写道:
人类的天子/享受的是兽类的威风/欣赏的是/兽性的美丽。
尤其是《兵马俑》,将自己人生的血泪浸透到描写对象之中,写得那么锐利而独特,完全没有我们听惯了的对那个王朝统一大世的讴歌和对那个军阵横扫六合的赞颂。他偏说兵马俑是秦始皇死后对老百姓部署的“一场地下战争”:
是嫌天才的书/还未烧尽?/是嫌读书的人/没有坑杀干净?/拳头大的心脏/狂想曲的血型……
胡征对诗美的追求,一开始就在中西结合的路子上进行。这种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西方诗歌的象征美、散文美,和中国诗歌的民歌美相结合,二是探索以现代诗歌的许多美学思维和创作原则来表现中国劳动大众的生活。
前面所引《石象》、《紫花藤》和《钟声》《挂路灯的》《思想家》这些四十年代的作品,都带有西方诗作常用的象征手法。但又与西方诗歌不一样,它表现的是当时中国革命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弃舍了西方诗作中的浮华、俏丽、艰涩,而以简朴明朗的诗笔写简朴明朗的民众生活和民众感情。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体西用”吧。
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所要求的过分拘束的格式与韵律,难以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人心灵的繁复,写现代生活需要更自由又更通俗化的诗体形式。但他又没有走当时(20世纪40年代)许多诗人所走的民歌体路子,而是汲取西方诗歌中对散文美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使外来形式和中国大众生活的质朴内容相通,熔铸成既有现代感又是通俗化的新诗体。

胡征和胡风(左)(1981年摄于北京胡风家中)
生命之花“开在碾盘下”
胡征是个有生命大痛苦最终却战胜了这痛苦的诗人。他的生命之花“开在碾盘下”。《碾盘下的青春》这样写——
一丛鲜花开在碾盘下/蓝的是泪,紫的是血,红的是伤疤/不怕霜打,不怕高压/青埂峰下将有异香喷发/迟开的花朵,晚熟的庄稼/种子埋得越深,生命强度越大。
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自喻。
胡征的生命没有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压抑中萎缩,诗的思考、诗的激情一直如地下火在运行。我们不妨看看在《致画家》中,碾盘底下压了近四十年的诗人,对艺术炽热的倾吐和对失去光阴执着地追索:
我借给你如火的诗情/你借给我如诗的画意/ 你借给我智慧的灵犀/ 我借给你鲜红的如液/ 我借给你多棱角的头颅/你借给我传神的彩笔/那么你我结伴同行/向宏观宇宙出击!
你爱色彩,我爱光/我爱奔驰,你爱凝聚/光原育爱,色哺育诗/一面奔驰,一面凝聚/那么,你我照色素的阶梯攀援而上/去追赶光年的足迹……
几十年的压抑、窒息,“如火的诗情”、“鲜红的血液”、“多棱角的头颅”,一切都没有变。“爱光”,“爱奔驰”,“去追赶光年的足迹”,也没有变。他以自己的坚韧战胜了大痛苦,得到了大营养。这自然不只是对诗的爱,而是对生命、对激情、对思考、对多彩的生活、对光似的目标的爱,是对攀登的、奔驰的、活跃的创造性生活的爱。
这种光阴稀释不了的爱,碾盘压不碎的执着,源于何处?

太行握别/你送我/一轮浩月/一树诗情/我送你/手枪一支/经书一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我天南地北/用汗水宣告/对诗的忠诚(《北行录》)。
是的,源于对诗歌——审美和生命——永不移翼的忠诚。
生命,有大痛苦始有大爱,有大爱始有大超脱。这是胡征以自己的诗向我们告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