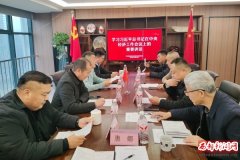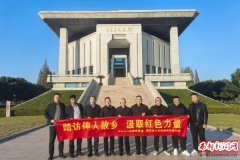粤剧行中讲起“笃爷”,几乎无人不识。笃爷,何笃忠也。当初我也叫得有点不太习惯,尤其数年前,他还算年轻,这个“爷”字可是上了辈份的称呼。但叫着叫着,似乎也就习惯了。尤其经常在红线女艺术中心召开粤剧工作者联谊会工作会议期间,红线女老师在叫何笃忠同志时,也会常常冒一句“笃爷系嘛?”听着叫着,就习惯了,反而对先前叫的“何老师”不习惯了。

果真“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我总想弄清楚:为什么在他二十多岁时,就被冠上“爷”的头衔?我曾经猜想过,粤剧行中人都把他称作“通台老倌”,会不会因为他“计仔”多的缘故,这“爷”字便从“扭计师爷”中得来。再打听,原来笃爷还有一本“威水史”——他是广东粤剧学校首届毕业生,曾得白驹荣、陆云飞、文觉非等前辈亲授。1965年至1979年在新会粤剧团工作,先后任主演、编导、团长,主演过《红灯记》《南海长城》《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剧,并编、导过《金种》《泪血樱花》《月难圆》等剧目。“文革”后又在全省率先恢复古装戏《搜书院》《选女婿》《苦凤莺怜》等传统戏,创造了在一个戏院里一日三场连满四十天的纪录。1980年调入广东粤剧剧院艺术室任编导工作,编演粤剧大小剧目近百出,粤剧电视连续剧十多部,大小综艺晚会更不计其数。其中,专题片《红线女艺术之路》与电视粤剧《连升三级》《七十二家房客》,还先后获得“星光”奖、“金鹰”奖。曾为红线女、罗品超、陈笑风、郑培英等粤剧名家艺术专场担任编导工作,著有《何笃忠编导演作品选》,在百集系列讲演《说戏》中,主讲其中粤剧卷(十集)。在他的粤剧艺术生涯中,不仅能得到众多前辈名家的指导,还与许多名家携手合作过,这些积累让后来者叹为观止。“笃爷”之名,源自他在基层剧团担任过舞台监督,行中习惯称舞台监督为“督爷”,而“督”与“笃”同音,于是人们干脆叫他“笃爷”。这一叫可不得了,从此世人只知有“笃爷”,却不再知有“督爷”了。
我是哪天正式认识笃爷,在什么环境下初次见面,已记不得了。也许由于他1980年代初便与电视结缘,在粤剧界中名声早播,特别是1990年代初,老少咸宜的电视系列粤剧小品《笑话百出》风行南粤,经常“霸占”着荧屏,不但粤剧观众爱看,外来工观众也喜欢,故编导演一身兼的“笃爷”便名声大噪。直到最近,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开车送他回家,连他所在的住有十多万人的“新村”保安人员,也能远远地热情呼叫“笃爷”。我也是早就闻其大名,只是无缘结识。直到与他合作20集的电视连续粤剧《四喜临门》(我任编剧、他任导演兼主演),以及他执导演由我改编的粤剧《珠联璧合》时,才有了愉快的交往。但那时还是“浅交”,未算真正走近他。
2004年起,经红线女老师提名,我担任了广东粤剧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从此工作接触多了,对笃爷的了解也就多了。2009年起,我接替笃爷兼任联谊会秘书长一职。这一接任,既是红老师的重托,更是笃爷的信任。因为我一直对行政工作不太在行,对联谊会的工作更是缺乏了解,许多的工作,可以说皆由笃爷来主理,他这个常务副会长,依然统理着联谊会的大小事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一个思维活跃,条理清晰,干事认真,多才多艺的何笃忠老师,慢慢从合作者到同事,再到知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粤剧戏行称他为“通台老倌”。“通台老倌”者,舞台上各种行当皆能饰演,编、导、演兼于一身之义也。他是演员出身,作为第一届粤剧学校毕业生,曾得白驹荣、陆云飞、文觉非等名师亲授,耳濡目染,对粤剧表演有深刻的领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会县粤剧团工作。
在当时,省剧校毕业的高材生下放地市及县一级粤剧团,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一大风景。诚然,基层剧团生活是艰苦的,条件也无法与省市大班比,甚至还会有大材小用之感。然而,当我们回望过去,“下放”就像一个炼钢炉,可以炼就好钢。数年后回来的他们,均成为了粤剧界新一代的顶梁柱。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下放”的历练,使笃爷在基层剧团中把主演、舞台监督、导演、编剧,甚至化服具、舞美全做遍,才练就“通台老倌”的本领。而笃爷的这些本领,除了在粤剧编导工作中出色地发挥着作用外,在《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的编纂工作中更显示出他的优势。因为他对粤剧音乐唱腔、锣鼓、排场、例戏以至各种名家的风格均烂熟在心,便在编纂工作中起到了绝对的核心作用。他的才华也在编纂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发挥。
想当年省粤剧院常提杨子静等“九老”,如今“九老”已一一老去,健在的林榆老院长也已是百岁老人。像笃爷这样有着丰富经验、深厚功底,更有一颗为粤剧事业执着滚烫的心,能言敢言的新“宝贝”,我想不仅是粤剧院的“宝”,更是粤剧界的“宝”。
能言,是一种能力;敢言,则是一种智慧和勇气。在如今“一团和气”戏剧环境中,真正的戏剧评论甚是缺失,充斥于现实的大多是虚假的宣传,对现实能言敢言,就显得尤为珍贵。如今,很少看到真正有份量的戏剧评论,尤其是粤剧评论。网络已有人批评,“逢演必轰动”“逢演必感动”“逢演必精品”,这种宣传,于出品方来说,无可厚非,但由于缺乏真正的戏剧评论,优劣无从分辨,到头来其实是对戏剧生态的一种伤害。这种口号式的宣传多了,就是“狼来了”的故事,观众不再相信公众媒体,宣传越轰动,越觉得欺骗越大,观众越不想走进剧场。说真话,真评戏,才会让戏剧回归常态。虽然“笃爷”不是戏剧评论家,但他知戏懂戏,真言真语。在“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中他是受聘专家,对年轻人的作品,他读得细,说得出不足,讲得出道理,出得了点子,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敬重。
和而不同,君子之交。我与笃爷自相识到今,有合作,有共事,有理解,有支持,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我们不会因为分歧而疏远,而是越走越近,如师如友。数年前,在一个以粤剧为由打造的项目中,我参加了粤剧部分的创作。该项目还未公演,却在迎新春晚会上,被主持人指鹿为马般把戏中一段与粤剧完全无关的唱段,说成是粤剧,还加上一堆“原汁原味”等溢美之词,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身在其中,当然不能原谅主持人“指鹿为马”的解说,那不是口误,而是无知。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无论报章和电视荧屏,这种“无知”现象太常见了。这场“风波”的是非我们先不论及,因为争论的起因与涉及的内容,它本质上并不是一部争论的焦点——粤剧,更不是一部可供示范的粤剧,它只是以一个粤剧人作为描写对象的、集话剧、音乐剧、粤剧于一体的旅游剧,除粤剧部分外,其余均以普通话唱念。它是一部集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旅游剧目,或者说是一个为粤剧做广告的“广告剧”。就如香烟广告“万宝路的世界”一样,用什么语言,以什么音乐,或什么画面做广告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让人记住有这么一个产品。广告上的香烟无烟也无味,不能吸食,也不说其特性,它只是一个让人记住品牌的广告词或广告剧。它和明确标榜是一台粤剧的创作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台完整的粤剧。这场争论存在许多误会的地方,我虽涉其中,但我依然认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在我们的一些创作实践中,的确存在这种去粤剧化的问题和倾向,作为粤剧从业者,应该允许各种探索,但不容许以粤剧之名把粤剧变成“非驴非马”的“怪物”。这种争论,对我们今后的粤剧创作是有警示作用的。争论,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不争论,不言语,只有一种声音,才是不正常的,甚至可怕的。我们期盼有更多良性的争论,即使也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但总比一潭死水好。通过争论,可以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广大,粤剧的传承和发展也更健康。我和笃爷的分歧和争论,基于如上观点和角度,和而不同才有了价值和意义,这种友谊才显得更为珍贵。

左起何笃忠、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梁郁南
粤剧是一个开放的剧种,集各种艺术大成之广府大戏从来就有如海纳百川。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大师,也从不固守,而是融汇南北的,但万变不离其宗。针对当前有些团体迷恋外请“大家”来替代粤剧人编演粤剧,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剧种特色,将“改造”视为“创新”的现象,笃爷曾用粤剧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什么叫文化自信:“回顾70年的粤剧创作,能够留得住、传得开的粤剧剧目,几乎无一不是粤剧人自己创作、打造的。”他从《搜书院》《柳毅传书》《山乡风云》《梦断香销四十年》《范蠡献西施》,到最近二、三十年的《南唐李后主》《锦伞夫人》《伦文叙传奇》《睿王与庄妃》《土缘》《梦•红船》等等剧目的传演,说明了粤剧本土创作的重要性。然而,特别是近来一段时间,“大家”越请越“大”,金钱越花越多,高价聘请的省外编剧写的往往只是“半个”剧本,还得花钱找人“翻译”成粤剧,这种北李南栽的怪现象司空见惯,地方戏曲越来越失去本土特色,越来越趋向“同化”,花了大钱、大力气却难见有留得下、传得开的作品。在粤剧行中浸了大半辈子,对粤剧历史有深刻了解的笃爷,通过主持复排《香花山大贺寿》和历数年执行主编《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等项目,目的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保住粤剧传统,留住粤剧的根。
俗语说,“家有一老,胜过一宝”。76岁依然精力旺盛的笃爷,可以说是粤剧一“宝”。最近,省粤剧院为他设立了“何笃忠粤剧工作室”,看了他列出的长长一串工作清单,老骥伏枥、退而不休的笃爷,令我肃然起敬,也足以成为后辈学习的榜样。
(本文发表于《广东艺术》杂志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