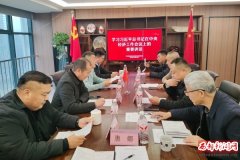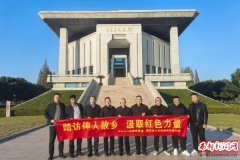西部新闻网消息:(文峰 华商报记者刘燕)核心提示: 父亲醒来后,周亚峰伺候了父亲几天就开学了。临走时,原计划要拿走13000元学费的周亚峰只带走了8000元。秋末时,乔淑惠卖掉了辣子和玉米东拼西凑,凑足了5000元给儿子寄了过去。周亚峰开学临走时,周红财和乔淑惠试探着问他考研的事,周亚峰一下就火了,“你们再给我备下30万我去考研、结婚、买房子”。周红财在病床上气得嘴直打哆嗦:“好,你在西安给爸瞅一个有钱的单位把爸放在门口让车轧死去,看给我娃赔上30万命价。”
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很多农村贫困家庭的父母通过供子女上大学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然而,近些年,扩招加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让这也变成了一项风险投资。在经历了子女被大学录取那短暂的骄傲和喜悦后,留给这些家庭的则是血泪交织下的负债,还有遥遥无期的守望。
在陕西省合阳县,党宪宗——一个小县城的商人和纪实作家,用近十年的时间,关注和追踪着这些家庭,完成了《沉重的母爱》到《沉重的回报》两部著作。他希望若干年以后,那些曾被供养过的孩子们能在记忆深处牢记父母的恩情。
29岁的周亚峰回到渭北塬上这个叫做万年河村的土沟沟已经俩月了。
8年前,考上西南一所大学的周亚峰曾一度让父亲周红财和母亲乔淑蕙脸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而现在,他们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万年河虽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沟槽地。
隆冬的塬上,沟槽地里还有稀疏的玉米秆子没来得及砍掉,地堰边野生的柿子树上零落地挂着几个柿子。回到家的这几个月,这个曾经让父母在全村人面前有过短暂荣耀的大学毕业生,每天拿着砍刀在地堰边砍着酸枣枝和柿子树杈。
干这样的农活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娃,即便是在大城市“历练”了多年,也没能改变这点。
60米的天井差点要了父亲的命
“你还认得我吗?”2011年12月22日,见到周亚峰时,69岁的党宪宗对这次意外的碰面有些兴奋。
纪实作家党宪宗八九年来一直关注这家人的境况,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已经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
一开始,周亚峰不言传,后来他扶了扶600度的近视眼镜说:“不认得。”2004年冬天,党宪宗为写一本当地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曾经造访过周亚峰的家。那时,周亚峰已经在四川一所航空学院读大学二年级,每年即便是省吃俭用也得一万多元。
那年,周亚峰的父亲周红财正是壮年气盛。党宪宗见到他时,这个当过兵的父亲很健谈,“再累再辛苦也一定要把娃都供出大学去,不欠账。”当周红财知道党宪宗是个作家时,很骄傲地向党宪宗透露自己的大儿子是个大学生。
这是一种怎样的骄傲?
在后来的纪实作品《沉重的母爱》一书中,党宪宗这样写到:农民大学生这顶桂冠是父母的血和泪交织成的!所以,这所谓的“骄傲”是流血流汗的精神支柱。
很快,周亚峰给这个家庭带来的“骄傲”又成了这个家庭后半辈子的重负。
周亚峰读大学的第三年时,父亲周红财并没有实现“不欠账”的愿望。
在万年河村这个靠天吃饭的贫瘠沟槽里,庄稼仅够口粮,父母怎能仅靠种庄稼来供周亚峰读大学,借账成了周亚峰读大学时学费的主要来源。
为了还账,乔淑惠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离村近40里外的合阳县城打工。周红财白天种地放羊,晚上就去地堰边的土沟和杂草堆里逮蝎子。在党宪宗走访的近百个渭北农民供养大学生的家庭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都有过逮蝎子的经历。
蝎子都躲在杂草最茂盛的土旮旯里,又只能晚上去逮,人不仅要冒着被蝎子蜇的危险,还要防着脚踏空从土堰上摔下来。每年周亚峰的学费,有近一半都是父亲逮蝎子三元五元凑起来的。
周亚峰第三年大学暑假,为逮蝎子,周红财不小心踏空跌进足有60米深的天井窟窿里,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才被人发现,送到县里的医院抢救了六七天,命才保住。
党宪宗在写这个故事时自己也落泪了:“中国的农民供个大学生咋这么难。”
这些细节都被党宪宗一五一十地写进了书里,只是人物都用了化名。
父亲醒来后,周亚峰伺候了父亲几天就开学了。临走时,原计划要拿走13000元学费的周亚峰只带走了8000元。秋末时,乔淑惠卖掉了辣子和玉米东拼西凑,凑足了5000元给儿子寄了过去。
周亚峰开学临走时,周红财和乔淑惠试探着问他考研的事,周亚峰一下就火了,“你们再给我备下30万我去考研、结婚、买房子”。
周红财在病床上气得嘴直打哆嗦:“好,你在西安给爸瞅一个有钱的单位把爸放在门口让车轧死去,看给我娃赔上30万命价。”
党宪宗猜测,这次很不愉快的谈话是促使周亚峰从2006年离家以后再也没回过万年河村的一个主要原因。
“娃呀,快好好上大学,等你毕了业咱家就不这么穷了。”那次临走时,周红财一再嘱咐儿子。
五年后大学生儿子终于回家
2007年的秋天,周亚峰大学毕业了。他毕业后直接去了南方一家外资工厂。
航空机械的专业让他在这家工厂从事着类似苦力的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1500元,周亚峰只做了半年就干不下去了。
2009年正月,大年初三,党宪宗去到周亚峰家里,那时,他正在筹划着写另一本有关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对家庭回报的调查,周亚峰是个典型。
隔了四五年,党宪宗再见到周红财夫妇时吓了一跳。
才刚刚50岁的周红财看起来足足有60多岁,“满头是灰,脸像陕北的枣树皮,看人时目光呆呆的”。
这家的面貌一点没变,原先的两面土窑现在只剩下一面,能住人的杨木厦房檐口苇箔全都裸露在外面。这次,周红财愤怒地骂了儿子,毕业三年都没回过家,顶多过年打个电话,也没给家里寄一分钱回来。
年三十,家里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老两口都不敢看,怕儿子回来晚敲门听不见。
“供儿上大学顶了个屁用。”党宪宗知道,一般儿女再不好父母也不会在外人面前骂,周红财是气到极点了。他告诉老党,他们还在还账,儿子大学毕业那年为找工作打基础又花去一大笔钱。
周红财只知道只要儿子读大学就能改变一切,可是儿子三年来似乎没有让他们看到喜悦,“家都不回了,他到底在外面弄啥呢”。
距离这次党宪宗到周亚峰家又过去了两年,大学毕业将近五年,周亚峰终于回家来了。但29岁的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没有女朋友,回家时也没给家里添任何东西。
从南方一家合资企业离开后,周亚峰去了广西,工作太难找,他只能摆地摊。
这是周亚峰第一次向家人讲自己的经历,他很拘谨,时不时看看对面的母亲,“这是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在广西,地摊生意也没能做很久,他又干了一年多的商场临时销售员。
追踪这个家庭这么多年,党宪宗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大学生多年来在外面做些什么。
再后来,周亚峰辗转到了云南,在一家通讯公司,他做着类似于推销电话卡的工作,这一次时间最长,将近两年。
记者再三追问,他才肯说自己能挣多少钱,“也就两三千的样子,吃住下来也没有多余的存钱”。
周亚峰承认自己的性格过于内向,找工作就是个障碍,他也想突破自己,“可是做着做着就坚持不了了。”毕业五年,他没给父亲买过一盒烟、没给母亲买过一件衣服,两个月前,周亚峰空着手回到万年河村。
儿不归,家散了
党宪宗说,在《沉重的回报》一书里收录的这些故事其实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书里故事总有结尾,但在现实中,人生还在延续。
合阳县甘井镇杨村,徐创明家供儿上大学的故事党宪宗用的笔墨最多。50岁的徐创明是二婚,自己本来就有两个孩子,妻子春花(化名)离婚后带着儿子徐磊从村东头嫁到村西头徐创明家。
党宪宗说,徐创明一家是渭北塬上最淳朴最善良的农民家庭,虽然徐磊是带过来的孩子,但徐家在支持孩子上学这件事上做得问心无愧。
徐磊上高中时,徐创明自己的两个孩子学习不好都出去打工了,徐创明和他六十多岁的父亲母亲不把徐磊当外人看,“娃上学好,全家人再苦再累都供他”。
后来徐磊上了西安一所民办大学。民办院校比公办的花销要多,徐磊上大学的那几年,姐姐和年迈的奶奶在河北打工,徐创明在山西打短工,家里的爷爷种地,只有过年全家人才聚到一起,数着各自挣来的钱给徐磊凑学费。
2008年,党宪宗第一次去徐创明家时,徐创明告诉他,徐磊大学毕业都三年了,不知啥原因除了打个电话几年都不回家了。
党宪宗听完很生气,他决定去会一会徐磊。在西安电子城的一家卖场,党宪宗好不容易见到了徐磊,“我现在这个样子咋回去?”没等老党开口,徐磊先问他。
原来徐磊上的这个民办大学根本就不是个正规大学,四年间,在校学习的时间没超过一年,剩下的时间都被学校组织去南方工厂打工。第三年结束时,徐磊就离开了学校,可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最后一学期时,他拿着家里给他的7000元学费原本想投资做个小生意,没想到却被骗进了传销窝。半年后,徐磊又问家里骗了4000元才从传销窝里逃了出来,因为欠6000元学费,徐磊连毕业证都没拿到。
第一年找工作,徐磊告诉家人自己分配到成都了,家人高兴地给他1000元“让娃安家”,实际上,他在一家茶馆当服务员,那次离家他再没见过家人。
等老党找到他时,他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我该不该把这些告诉家里人?”讲完故事,徐磊直戳戳地反问老党。
等老党回过神,徐磊已经走了。一个月后,老党拉着徐创明来找徐磊时,徐磊辞职已经半月了。
两年前,徐创明的老母亲去世,偶尔徐创明会把老人的去世归结为“那几年为供娃上学劳(累)的”。已经7年没和家里人联系的徐磊让自己很恼火。徐创明怀疑徐磊可能私下里只和母亲联系,因为徐磊不是自己亲生的,这直接导致他和妻子春花的关系日益恶化。
半年前,春花离开徐家不知去了哪里,这更印证了徐创明的猜测,“去寻娃了”。
黑瘦的徐创明现在和年迈的老父亲住在一起,每当老父亲冷不丁提起当年全家齐心协力供徐磊读书的事情时,徐创明就会找个借口把话题岔开。
“不要娃的一分钱,他(徐磊)是大学生我是农民,该不该回家看看的道理,他应该比我明白。”临别时,徐创明突然对记者说。对党宪宗来说,《沉重的回报》是比《沉重的母爱》更难落笔的纪实报告,因为“父母之爱源自天性,儿女的回报却受限于道德的评价,很难衡量对与错”。
党宪宗所在的合阳县堪称省内的高考大县,这个贫穷的小县城每年要走出去近3000个被录取和自费的大学生。土地的贫瘠促使着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上学改变命运,再苦也要让娃读大学。
“这是文明的喜悦,亦是哀伤的渊源,”党宪宗说,在时下这个中国农村面临大变迁的时代,读书的概念在父母的心目中还是那么纯净,但在孩子这一代却和更多的物质价值掺杂在一起。
因为写书,从2003年开始,党宪宗筛选了一百多户渭北塬上农民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在一行行的文字里赞颂着这些大学生的父母,追踪着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回报给家人的喜悦、惆怅和失望。
他的故事里,有一手捂着6000元学费,一手拿着冷干馍躲在墙角啃的父母;有起早贪黑卖豆芽供孩子上大学至今仍不知羊肉泡是啥滋味的父母;有毕业后毅然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回来照顾父母替父母还账的大学生,但更多的却是大学毕业后仍需要被父母供养的莘莘学子。
2009年,党宪宗策划写《沉重的回报》时,一些大学生写信给老党:“你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有多难,就业难、结婚难、买房难……”老党回信:“大学生的难,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是为攀比白领生活难,而父母的难是为了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终止,把幸福留给孩子。”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因为喜欢曹植的这两句诗,老党最关心孩子大学毕业后有没有回家看望父母,有没有卸下父母的重负。
合阳县西郭村是全县有名的大学生村,全村500多口人,有100多个大学生,有些人家甚至供养着超过两个以上的大学生,党宪宗的很多故事都采自这个村。记者和老党去采访时,偶尔见到手拿?头的沧桑面孔,老党总会主动发问:
“咋还辛苦呢?旧房修复了没?娃经常回来不?”
“不经常回来,不辛苦咋成,娃在城里要娶媳妇买房呢!”
西郭村的张永庄老汉是村里最荣耀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大儿子张亚斌考上了北师大,小儿子张亚文考上了北大,现在两个儿子都留在北京工作。
通过电话,张亚斌告诉记者,当年自己上大学,学费主要靠父母种地、借钱,还有一部分是靠自己暑假时去工地当搬运工挣的。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始供弟弟张亚文读书,弟弟毕业后,兄弟俩一起帮父母还清了上学借下的债务。弟弟现在是北大的博士后,经常去国外,两三年才可能回一趟家,而自己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每年也只能回一两趟家。现在他和弟弟每月都会给家里寄两三千块钱,但他知道父母一个子都不会多花。
党宪宗《沉重的回报》收录的故事里也有张亚斌熟悉的同村人,对于“回报”的话题,张亚斌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希望自己的状况很好才回家,因为回家也受到经济的影响,不仅要看父母,还要去看亲戚朋友,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对此自己深有感触,所以“回报父母”对80后的大学生很难。但他知道父母并不全都需要物质上的回报,更多的是“孝心”带给父母的慰藉。
今年上半年,张亚斌和弟弟给父母盖了新房,而此时母亲脑溢血的病却加重了,不能下地也说不了话,每天床头挂着输液瓶,不能离人。
采访时,当听到记者问自己的孩子,张亚斌的母亲突然呜呜哭了起来,这个曾经身板硬朗的女人现在只能听不能讲。张亚斌的父亲张永庄说,老伴想两个娃了。

大学毕业5年后,因为工作不顺利,周亚峰回到贫穷的家里

50岁的徐创明盼望儿子徐磊能回家看看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