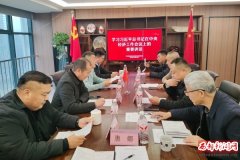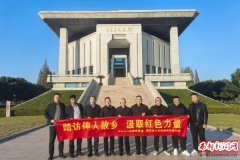西部新闻网讯(记者 唐晓楠)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惟金庸名头最盛、享誉最长,横扫华人世界。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十余年间写下15部作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联中的14个字,正是他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一部不在其中的,便是《越女剑》。

金庸以94岁高龄逝世,对全世界的“金迷”而言,无疑是让人悲恸的大不幸事。一时间,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大侠”的悼念,同时也在追忆自己的青春和过往。
虽然“大侠”这顶帽子最常见到人们往金庸头上戴,但显然并不适合他,因为从身份上说,金庸是个文人、作家;在文学创作而言,他的成就绝不囿于“武侠小说”。
但是,称呼金庸为“大侠”,又分明是合适的,这固是因为读者对金庸和他的作品太过喜爱,也是因为金庸一生之志,实不仅仅在于小说或文学,他有极高的政治抱负,他关注社会民生和文化传统,他热烈赞美自由,他以写小说的方式来描绘和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和家国,并将侠义之道贯注其中。
学者龚鹏程认为,儒和侠本来是不同的生命形态,但儒家学问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刚毅之行,勇决之操,近乎侠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叫金庸一声“大侠”,实在合情合理。

1955年,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四年后,这位作者和他的同学合资创办《明报》,自那以后,“报纸”和“武侠小说”成为金庸身上最具标志性的标签。作为评论员和小说作家的金庸,借助不同的文学体裁和大众媒介,表达观点、抒写情志,活跃在政治和文学之间。
以后来的眼光看,初创的《明报》尚未脱离小报趣味,为了生存和立足,除了小说、艳史和小道新闻之外,并无太多有价值的严肃内容,正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有关“逃港潮”的报导,让《明报》的面目焕然一新。

《笑傲江湖》写人性,阴暗之外也有光明,比如令狐冲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刘正风和曲洋对友情的执着,任盈盈对令狐冲真挚的爱恋以及仪琳对令狐冲圣洁的爱慕,这些无不带给读者感动和喜悦。
金庸本人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政治爱好者”,作为报人,他不可能像学者余英时那样只对政治抱有“遥远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后,金庸见过胡耀邦,1981年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表示自己是金庸在中国最早的读者之一,“文革”后期,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与邓小平会谈之后,金庸兴奋不已,认为他有魄力、有远见,称其像他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因为受到佛教影响,金庸后期的作品更显厚重,如那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天龙八部》,充满悲剧的崇高感。在97版TVB《天龙八部》连续剧中,由周华健演唱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可谓巧妙而完美地诠释了小说的隐喻与主题,悲欢荣辱、爱恨情仇,就像难解的题和难念的经,缠绕住人生和命运。
有意思的是,作为封笔之作,金庸的《鹿鼎记》又塑造了一个无比荒诞的世界,这看似不可理解,其实恰恰是现实的反映:虚构而成的武侠小说与读者之间本来存在陌生感和疏离感,作为“小流氓”和“反武侠”的主人公,让文本具有更强的现实基础;因兼具多重身份和多种技能(伎俩)而如鱼得水的韦小宝这一角色,不仅足以消除金庸以往小说中民族国家情感的死结,也预示着“适者生存”的时代即将到来。

正如陈世骧在给金庸的信中所称,金庸的小说“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这种“本真”既是文学的本真,也是人性的本真,更是世界的本真。金庸的作品早已超越了“雅-俗”和“新-旧”的二元,更因其自由的精神和高贵的理想而突破时空的框架,展示其持久的文学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