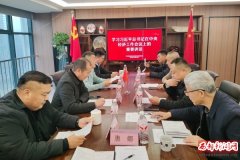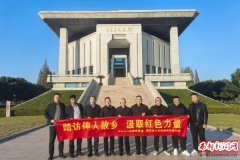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文/肖云儒)我曾经三次到迪拜,一次住了几天,两次是过境。今天万里行团队通知,我们要从迪拜转机去印度新德里,就是说,我有缘第四次在这个全球闻名的奢华之城落地了。
这个消息在全团引发了例行的骚动。几乎人人开始给亲友去电话和微信:“要在迪拜转机,呆几个钟头呢,家里买啥不?尽管说,快。不问迪拜都有什么,人人认为迪拜什么都有:也不问迪拜东西贵不贵,不贵还是迪拜吗!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记得我第一次是2012年夏去的,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组织的“中国书画世界行”活动,由当时全国美协副主席、著名藏族画家尼玛泽仁和我带队——一个攻美术,一个攻书法——先到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中国书画展,并与当地艺术家交流,然后从那里直飞迪拜,
到达时,星月已经将银光闪烁的黑紗披在整座城市之上。大家来不及进宾馆,直接去美术館布置展览。第二天开幕,大使馆文化参赞出席,迪拜当地的艺术家和观众来了不少,我还是第一次与穿阿拉伯袍的艺术家交流,感到很是新异,也了解了不少情况。
《中国书画世界行之迪拜》展览之后,团里安排大家在迪拜市区转了一天,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把迪拜传说成一个神话,都蜂拥着往这里跑了。最让我震惊的,是在某大商场,有像卖饮料似的自动售货机竟可以买金子,你只要刷够了卡,金戒指和小金砖便掉下来,随便取走!我还没有受过财富如此巨大的震撼,当时瞠目结舌得一定像个儍瓜。他们这里原来是把金块、金条当包金巧克力来消费的呀!
第二天画展组织大家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观。但我有一位朋友是原中国驻该国大使馆一秘——陈秘书。他已经不在使馆供职,成了专司北京和迪拜之间经贸的企业家。陈秘,其实应该称陈总,我还是称陈秘吧,陈秘第三天直接把我们三四个人(除了我、尼玛泽仁主席,还有一位女士,江苏镇江市美协主席)拉到他的住所,用他的私人游艇带我们去海湾观光。据说这艘游艇值三四千万!在迪拜,房子、车子已经不是财富的标志,大概只能算得上小富,游艇才是高档的奢侈品。有游艇还只能算中富,有游艇还有码头,尤其是有自己家庭的专用码头,这才算大富。当然这只是从民众可见的不动产来衡量,并没有把他们全部资产算进去。

这位陈秘我猜可能进入大富级别了。他的住所是三层楼的小花园,屋里摆了很多文物古玩,外行人也可以感觉出来那奢华的程度。叫我吃惊的是,他的园子整个由智能电脑全自动管理,每天傍晚,就会启动自动换水功能,自动喷泉和滴灌开始浇园子浇花,游泳池也会开始换水,水温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和主人的要求来设定。这是我把他家不叫家,而叫“住所”的原因---实在太像“八星级”宾館,而少了我习惯的家庭气息。陈秘说他们这条街都这个水平,“我当然并不是最出众的。”
他让我们看了他家颇引以为荣的一辆车,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有种叫兰博基尼的豪车牌子。回国后我给年轻人说起兰博基尼,他们的反应都是“哇”的一声惊叫。我不会开车,一点不懂车,但这次却开了一个许多铁杆车粉都难得遇上的洋荤。只见陈秘将车发动后,随意按了一个按钮,当即让我大惊失色,那“兰博基尼”竟然悄无声息就把前挡风玻璃和四个门再加上顶篷全部张开,像个男神扎煞着胳膊扬起了四五只手!瞬间便成了完全的敝篷车。我像年轻人那样喊了声:“好刺激!”
陈秘专门顾了两个佣工看房子,打理游艇。去个电话,在我们到之前游艇已经冲洗得层尘不染。那游艇分三层,上层是阳台,可以迎着海风观光、日光浴;中层是一个大客厅带厨房酒吧卫生间,可以自己做中西餐,调兑酒,开派对;底层是个大卧室,双人床带卫生间。我们在中层聊天看海景,陈秘不无炫耀地介绍他的创业艰辛。他用一句口头禅传达自已作为成功者的矝恃,说一段便要问大家:“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他并不需要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些被奢华震慑的朋友不会说半个不字,只能点头称是。
倒是他刚从伦敦留学回迪拜度假的女儿,一位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独自背对我们坐在船头,让海风把她的长发象旗帜那样撩着飘起来。她对父辈由创业到奢华的过程不感兴趣,她还是做梦的年纪,坐在船头不知道在冥想什么,大约是在圆年轻人心中那种常见的小资梦幻吧。那天有轻度的沙尘暴,要不是我在画报上已经很熟悉了迪拜风景,实在有一点索然寡味。
在海湾没多羁留,便绕一圈迳直回到他住所的码头。——迪拜的港湾,在这片富人区,整个结构设计成鱼脊骨形状。海湾是条主水道,两面发散出去很多小的水巷,每一个水巷通到一栋别墅面前。也就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直通大海的港囗,从这里登上游艇就可以直接驶进波斯湾。
主人看来是要在远道而来的国内朋友面前亮一手了,晚餐隔了很长还不开始。在等候晚餐时,陈秘带我们在街巷上走了一圈,他漫不经心的说着,但是字字如“金雷”(不是惊雷)敲击我的耳膜。手一指说,这是泰国总理他信的别墅,又一指说,前面那栋是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的,拐个弯又一指,成龙的!……此时整个街巷静悄悄,没有人也没有车,但有交警。

我问这些别墅常有人住吗?他开始没有理解,说当然有,天天都有人。后来理解了才补充,:是他们的物业管理团队常年住着,每栋别墅有三五个人呢!一个打理游艇,一个管理车辆,每家都好几辆车呀,还有打扫卫生的。至于主人们,“一两年不露面那是常事。入住率?百分之一、二,就要感谢真主!”
有房有车有游艇、有花园有游泳池,一切满足人高档欲望的东西应有尽有,但是没有了人!没有了已经创造它们、应该享用它们的人,所有的风景和设施便没有了聚光点,没有了核心,没有了光彩和灵魂!整个街巷非常寂静、除了我们几无行人,也没有家常生活必不可大的种种气息。
这是一幢幢珠光宝气却被遗弃的房屋,一个个青春年少却被遗弃的妇女。
一条被遗弃的小巷,一条没有生活因而也就没有生气的弃巷!
它们的主人都是人生的大成功者,二律背反的是,成功者的人生追求奋斗而不是享用,在政坛(他信)体坛(贝克汉姆)艺坛(成龙)的拼搏奋進,而不在别墅和游艇的光阴消磨,这样,主人怎能光顾,又谈何恩爱?被世界宠爱着的主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风光正盛,又怎能来与你厮守?只好自闭于奢华的居所,独守空房了。
其实,对于财富对于享受,那观念是人人相异、因时因地而变的。一个流浪者在寒冬找到一个麻袋会非常珍惜,会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睡在人行道的暖气盖上,自感幸福。而当你的财富多到消费不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消费时,便容易将这一切弃之如敝履。财富开始徽号化,由享用的对象变异为证明你身份的标签。那些佣人,那些房子车子,那条寂寞的小巷,都只是在证明和守护着主人的一个标签:富有者和成功者。对主人来说,这标签比其他所有的加到一起重要得多。
从那次开始,我对于迪拜就生出了一种心理上的拒斥感。以后两次來这里转机,大家都兴奋地策划着采购,要怎么以刷卡来满足自己的购买欲,又以购买来验证自已的成就感。我总是抢着说,到了迪拜机场,你们把所有的行李都给我,我看行李,我一步都不会离开。朋友们很奇怪,善意地问:不给家人买点什吗?我说我们家三代都不需要。第三代还小,穿名牌会误导了他们;第二代,儿子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儿媳对于爷爷的购物缺乏起码的信任感,未必满意;第一代,我和老伴,不品牌的人和品牌的衣物怎么能搭调得入时入调呢?所以,在迪拜机场我最“物尽其用的岗位就是死守行李,当一个忠实的“行李寄存好老头”。富可敌国的人可以像贝克汉姆一样,随意抛洒豪华,不富裕的人只要愿意,也可以抛弃迪拜。将迪拜那些用金子打造的街道在内心变成一条“弃巷”就是了。
迪拜少有自然景观,更无历史人文景观,它完全是人造的,是用钱堆出来的一种极至性的生存体验。如果说旅游是一种时空快速置换的生存体验,我们去迪拜,由常态生存遽然置换为极至生存,便跟一种我们生活状态相距甚远的,崭新的生存环境做了一次跨文化交流,获得一种惊喜和惊悚的满足。在这个角度,也唯有这个角度,迪拜才是有意义的。
正在浮思联翩,万里行团微信群通知:由于航班安排有变,我们将由阿拉木图转机德里,迪拜去不成了。我心头很自然地冒出两个字:也好!
在迪拜面前,我就这么“阿Q”着,“阿Q”了十多年。我和这座城,至今相看两不厌,也相看两无碍,谁也奈何不了谁!(2016月11月26日 新德里 高天远云忆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