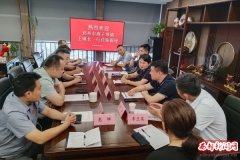涅克拉索夫在1858年的一首短诗中写道:“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你是活生生的见证,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骤起的不幸时分,你撞击着人的心底,犹如波涛撞击着峭壁。”百多年后,以同样博大的悲悯情怀,路遥用心血结晶的《平凡的世界》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哲理性思考:“活着,就要时刻准备承受磨难”。陕西人艺将他的这部作品改编为同名话剧搬上舞台,让许多观众享受到话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引发出非同一般的热烈反响。

四对爱情与三层含蕴
把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搬上话剧舞台,严峻的课题是,如何用话剧思维,把百万字的文学故事重新提炼成只有3万字左右的戏剧故事。所谓“戏剧故事”,就是要讲求集中性、动作性、直观性以及戏剧性故事。为此,编剧孟冰选择了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史,作为全剧架构的支撑。
小而言之,这是表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爱的觉醒。改革开放的初期,突破僵化思维方式之后,承认个人自身的正当利益,特别是追求爱情的权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下就燃烧起来,而其中向往美好爱情的火焰大放异彩,是那个时期的鲜明特征。剧中选择的这四对青年男女,他们或真挚相爱,爱得生死不渝,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或相爱不成,只得无声吞咽苦果而强颜无事,如孙少安和田润叶;或爱恨交错,冷热相反,无以自拔而历经残酷之后的重新相识,如田润叶和李向前;或过于“清醒”,把糊涂当成明白,历经苦难而终遇真爱,如郝红梅之后遇田润生。这中间还穿插着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夫妻情深,孙少平对班长遗孀的怜悯爱护……而其中的核心是孙少平与田晓霞。他们的追求代表了那一代青年向上的精神,他们的爱情显示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纯真。四对青年男女情感上的戏剧性变化,演绎在同一块饱含悠远文化和苦难历史的黄土高原上,他们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欢乐与悲伤显得格外苍凉,格外催人泪下。
大而言之,爱情中的“政治经济学”道出了改革的起因在于人心。田润叶的那封信,“我愿一辈子和你好”,使得孙少安的生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然而一转眼,此事就化为乌有了。孙少安的一句简简单单的问话,道破了他与润叶的爱情有花无果的残酷现实:“你说,我们结婚以后,是我去县里跟她住学校的宿舍,还是她回来跟我住牲口棚?”城乡二元化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岂止是“农”与“非农”的户籍差别?爱情被非感情的贫穷活生生地掐死了。
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爱情、事业、命运为主线的全剧,始终在理想的美好世界和平凡的现实世界中间跌宕着,翻腾着,挣扎着,奋斗着……诡谲的命运使得孙少安、田润叶、郝红梅在坚韧、吞咽、探寻、挫折之后,终获安然。而孙少平总是在思索许多困惑,总是在探寻未知,总是想知道在更大的世界会发现什么。他非常知心地对田晓霞说,“只有像你我这种人,看了一点书,就开始探讨人生,甚至觉得自命不凡。可问题是,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却改不了,打死也不愿意同流合污。你说,这可怎么办?”他们俩就像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里的小男孩,离开丑恶,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当田晓霞真的为了高尚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的时候,正如孙少平在小说中读到的,“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古今中外,所有为美好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人莫不如此,只能是留取丹心,与天地恒存了。全剧的最后一个场面是,孙少平把去年与田晓霞的会面与现在对她的缅怀糅合在一起,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寻找着,伏在浸透苦难的黄土塬上呼叫着心爱人的名字“田晓霞——”那就是在呼叫着他日夜向往的理想。
“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那是因为平凡世界的人们从未停止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他们像但丁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活得平凡,但我们绝对不能活得平庸。这就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所昭示的深蕴。
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史蕴藏着三层内涵,是孟冰在全剧架构中的独特建造,是全剧创意的精深表达,是对全剧主要人物形象的精妙雕琢。
大胆融入象征元素
导演宫晓东在这部戏里做了精心而大胆的创造性探索,使自己在导演艺术的攀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键是他在转台的使用上,显示了新的解读。
剧中,宫晓东让他的转台负载着富有哲理的象征性含义。J·L·斯泰恩认为:“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和契诃夫,当他们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却仍力求选择一种更加象征化的表现手法”。譬如,易卜生在他的剧作《野鸭》中,“贯穿全剧的则是野鸭本身,它是象征着罪恶的一种难以捉摸的符号”。契诃夫的《樱桃园》中的樱桃园,负载着多重的象征含义:俄罗斯贵族曾经的美好生活写照,一面检验人生态度的镜子,还是承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些就是为了在戏剧里“追回那曾经在现实主义中失去的梦幻色彩”。一旦戏剧舞台失去了“梦幻色彩”,就等于弱化了剧场艺术的魅力。
宫晓东在转台使用上营造的“梦幻色彩”是什么?就是孙少平的那句话:“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只有细心观察生活,深刻思辨生活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认识。当美好和痛苦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换相连;当理想与现实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生悖反;当清纯与混沌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依角力,都具有如梦如幻的色彩。
磨盘和碌碡是黄土高原上农户最常见的劳动工具。这出戏的整个舞台就是一座巨大的磨盘和它托着的碌碡,核心就在一个“转”字上,转出了平凡世界里人们的挣扎、痛苦、奋斗、快乐、思辨……孙少安刚刚读过恋人田润叶誓言般的情书,发狂地大叫“大山啊你挡不住云彩”!可磨盘一转,他就去山西相那个不要彩礼的贺秀莲当对象。磨盘再转,田润叶就成了婚礼上的宾客,她送的一块红缎子,竟成了新郎与新娘入洞房的盖头。命运仿佛就是一个熊孩子,用手指轻轻一转磨盘,人们就这样地被撕扯着折磨着,就像上面的碌碡变成洞房那样乖张、荒诞。
特别要说的是,还有不转之“转”。孙少安与贺秀莲那幅婚礼的巨幅画面,生动、逼真、丰富。此刻,整体磨盘并没有转,但是,这幅画面却不时地在上下流转。它上下三层——最上的碌碡,那是洞房;中间是磨盘,那是婚礼主会场;下层是磨盘基础,由盘旋而上的小道缠绕着,小道侧面是两口窑洞门。
结婚现场总氛围就是喧闹(乡亲们自带着大海碗,拥挤在这里,吃着油泼辣子面之类的流水婚宴),它分布着九个视点,显示着多种不同的喧闹。在这样一幅相对静止的画面上,导演不动声色地让整幅画面上下“流转”,即连缀起来——先是妇女干部,同时又是大媒人的二妈走进二层婚礼主会场,面对三层场面,大声为新娘子造势,威风地将手中的一卷纸(像是文件)拽到一层小道上低头吞咽面条的后生的头上,提醒他注视“领导”讲话。之后,那后生再把那卷纸递上去。这拽下和递上,是第一次连缀大画面。田福堂告知新郎,润叶可能回来,提醒他做好准备,之后,顺着小道,从二层到了一层,拍了拍在最底层,搀着奶奶的少平(为后面黄原饭店那场戏作伏笔);再一抬头,撞见进门的儿子润生,骂了两句儿女都不省心之后,扬长而去。这是第二次连缀大画面。润生扛着自行车,顺着小道,登上二层,向新郎表示祝贺,这是第三次连缀大画面。这三次反复连缀,使整个大画面浑然一体而又灵动活泼,为即将开场的,田润叶与孙少安那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对撞,营造好阔大的风俗环境,创造出特有的意境,既刺激又规定了两位主人公的内外表现:教师田润叶只能孤独地苦笑无语,默默吞咽;新郎孙少安只能孤独地用佯作的狂喜呼叫来怒斥命运的残酷,暗中倾吐内心的苦闷。而这里,动与静的对比,欢乐与痛苦的对比,喧闹与孤独的对比,不正是孙少平对人生的总结——“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磨盘与碌碡的左右旋转,巨大画幅的上下流动,在运动中编织出了悠长的、含蕴的、厚重的、无尽的、梦幻的画卷,令人看不胜看,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平凡的世界》的编导在自己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中,张开想象的羽翼,大胆融入象征的元素,显示了他们不断强化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力的自觉。观众的喜爱证明了这种探索是成功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剧中看到生命的光芒:理想使痛苦光辉。(欧阳逸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