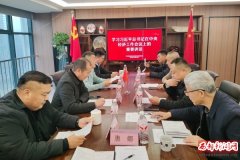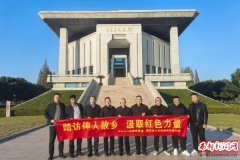作家李喜林
奇特深邃的意象
《知了》是陕西实力作家李喜林的最新作品,发表于2016年《延河》文学月刋9月号上,写的是作家自己的一个梦魇。写知了,又写的不仅是知了。小说中的“飞床”和“知了”、树等意象奇特深邃,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一)、“飞床”意象:灵魂由完整走向破碎的象征
先看小说写了什么。小说首先展现的是时间的维度。由当下回到过去,主人公可以透视到自己的童年和过去生活的印记。第一段的“楼层”显示出“我”是在都市生活,随着梦靥,以灵魂形式回到故乡并与父母相遇。这种相遇很奇特,是一种以“床”为载体的灵魂之游。在灵魂之游过程中,空间维度出场,先是老家后院,能看到小时候的推碾子的情景,而碾场成了别人家的庄基地,很快消失了,被新建的二层楼压在下边,不存在了。
“床”又飞到饲养室,又一个记忆出来了。爹和我光身子在饲养室。似遇鬼一样,饲养室里的驴受到一种惊吓,开始用蹄子胡乱刨挖,父亲用棍子打驴。后来,饲养室被新盖的房子占了。
“床”接着飞,飞到家乡涝池边。涝池边曾经有劳作的母亲。“涝池干了,如同一张巨大的嘴,吞吃着土和瓦砾,吃满了,被楼宇压住,嘴依然张着。”涝池也正在消失。像大锅一样的涝池,被填了。也被楼房占领了。
涝池消失了。载着“知了”父母和“我”的“床”又开始飞向皂角树。而皂角树也正在消失,消失在没有声音的夜色里。
皂角树消失了,“知了”还得找树。村北有个古槐——象征村树和社树的古槐。寻找古槐树的过程中,原来固有的路径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飞床找不到原路,一下子撞在墙上。
古槐也消失了。“古槐终究被连根拔起了,在接下来的身首分裂、支离破碎中,一条黑灰色的如同钢铁般的路穿过来,古槐随之消失在路下。”尽管我和知了父母等那么多的生灵都在拼命给古槐加力,古槐最终还是被连根拔起——一条路过来了,一条坚硬的路,直直地过来了,把原来的古槐树压在了地下。村子的根、村子最后的印象,也被连根拔起,连渣渣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消失净尽。
雍河是象征故乡的最后一条河流,是“我”的母亲河,原来有茂密的树林和水。“知了”爹娘说去雍河吧。“飞床”又开始飞了。故乡的老鼠等生物因为环境改观都没有地方依附,包括知了,所有的生灵开始大迁徙、大逃亡。而所有的动物都把“飞床”当成了诺亚方舟,都想挤到“床”上来——所有的动物,包括知了和小时候的麻雀都来了——以灵魂的影子出现了,“床”加重了,离地面近了。“床”承载的太多,甚至鼠类也蹦跳着想上来。“床”下面附着的一些生物被挤掉了。“床”变轻了。“床”又开始飞了。但却只剩下了床板。
到雍河去的“床板”已经薄如蝉翼。而原来浩瀚、宽广的雍河也变小了。水也开始消失,变得很瘦很瘦。很快,雍河里连水都没了,雍河河床都能开车,雍河正在消失——这种消失是致命的消失!“床板”飞下去的时候,河里没有水了。水干了。我跟“知了”爹娘也坠落下去。刚好掉在树上。已经化身为知了的爹娘吸食树浆之后很快精神起来,但是“我”却渴得不行了!忽然想起雍河岸边,“我”和乖凤曾经待过的窑洞里可能储藏有水。然而失去雍河水的参照,唯一的希望窑洞已经变成了“迷宫”,找不到了。
小说里主要意象是“飞床”。众所周知,床是一个家庭里最基本的东西。有了床,才有男女,才有孩子,才有家;有了家,才有了村落和社会,才有了世界,才有了繁衍生息。“床”一开始在故乡后院那个地方,出现时悬在空中,就像阿拉丁神话中的飞毯一样,但是这个小说是写一个“飞床”。“知了”爹娘和“我”就栖身在床上。代表已故的亲人的爹娘以知了的形式在“床”上和“我”的灵魂相遇。在小说中,载着“知了”父母和“我”的“床”一直存在,一直在飞,“我们”共同经历了古老的乡村记忆被粉碎,消失的疼痛,都共同承受到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知了的主要特征是“上树”,“床”也就在树根和树杈上或飞或停。我们说,“知了”和“床”都是记忆中的东西,是乡村的象征。床和蝉就这样建立起了联系,在不停寻找、碰撞过程中,飞床变成蝉翼,最后也消失了。还应该看到,“我”(包括父母在内)在“床”上出生,最后也要在床上走向死亡,“床”是肉体和灵魂寄身之所,是“我”最深切的生命和生活记忆,就像脐带一样,“床”是连接“我”、父母和故乡的主要载体。人离不开“床”就如同而知了离不开树,其更丰富的意义在于,有爹娘的地方就有故乡。从一开始还完整的床,到遍体鳞伤的床,再到床板,再到薄如蝉翼的床,直到消失,其实正是“我”的精神被撕裂、灵与肉被煎熬、精神溃败的全过程。“床”最后消失了。“我”也魂消魄散了。父母也以知了的形式消失了。故乡原初的东西都不见了。整个小说对过去生活进行了怀念和追溯,写出了灵魂的破碎和无法释怀的乡愁。
(二)、“知了”意象:故乡“故人”系列等的全息缩影
知了当然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小说中,爹娘是以“知了”形式再现的。“知了”爹娘开始出现,是在后院飞旋起的床上。小说最早起于对已故的爹娘的怀念。爹娘分别居住在“我”的左耳右耳,以耳鸣声音形式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小说中,爹娘先是在耳朵里居住着,有一天从耳朵飞走了。在特定的梦靥中、特定的时间段、“我”以灵魂的形式和父母相遇。我们知道,知了首先以蛹的形式在地心蛰伏、存在。雄知了发声,雌知了不发声,雌知了是雄知了的影子。知了的特征离不开树,靠吸食树浆,不管在哪,主要在树上生存:树根或者树杈上。“上树”是知了的基本特征。作家紧扣“知了”特征,精细描画。生产队饲养室,爹身体呈“上树状”;涝池消失之前,千钧一发之际,“爹抓住了娘的手,娘上了我们的床,在我的另侧,腿脚蜷曲着抓挠我像上树”。我们的床在去往古槐的途中左碰右撞,……爹和娘都打着寒颤,我将娘搂在怀中……娘像一个小女孩依偎在我的怀里。娘的两道柳叶眉像蝴蝶扇动的羽翼,似乎随时会飞起来”。古槐倒下之后,找不到栖息地的知了乱成一团,“庄子的上空飞满知了,知了与知了相互碰撞,看起来是一个个细小的影子,相互穿梭相互重合。”原来树木茂盛的雍河只剩下了残存的树木“我们落在了一颗柿子树上,爹娘瞬间与树胶着,干裂的嘴唇紧紧黏贴在树干上,在啃树。”可以看到,作家处处围绕知了在写,“知了”父母原来依存的树、土地、水都不见了,被现代文明侵占了,就连他们自身也面临被捉被爆炒的命运。
我们说,“知了”是一个高度浓缩了的文化意象,主要指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也包括灵魂无所附丽的“祖灵”们在内。小说完全将知了人格化,把写实和写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值得思忖的是,本应该和父母一块变成知了的“我”却始终保持着人的本色,这就和卡夫卡的《变形记》迥异,表明了作家始终是以上帝之眼,在清醒地俯瞰农村,看故乡,看社会变迁,尽力想把自己的灵魂剥离出来,拉开审美距离进行关照,悲悯、同情不言而喻。“我循声望天,泪光中全是飞翔的知了和知了飞翔的影子”。在此,我更愿意把这段话理解为对父母的思念,对故乡美好生活的怀念,对当下被破坏的生命景象的一声控诉和叹惋!失去土地的“父母”们已经被异化了,活在煎熬中,而这种憋屈的不很优雅的活,也将遭遇到危机!作家想念父母,想念家乡,怀念着过去和父母一块的亲情和无法回去的幸福岁月。
文末那些闪耀的手电光,也应该是外来力量的象征,包括革命在内,各种力量的介入,直接打破了中国农业社会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局面,在加快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同时,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比如醇美的人性、比如亲情、比如祖荫,比如总是想离开她、真正离开了却不时回望,心心念念的故乡……
(三)树意象:故土、故物等故乡之“根”的折光
除了“飞床”和“知了”,树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意象。因为知了是昆虫,必须依靠树来生活。知了是从土里产生的,把卵产在土里以后,很快变成蛹,再变成小知了,贴在树上,靠吸食树浆,而活着。知了离不开树。“上树”是知了的基本姿态。树是知了的环境。所以小说时时刻刻把“树”作为重要的描写对象。
“树”最初出现,还是“我和爹在后院悬空的床上睡觉,爹身体呈上树状”。后来,“夜还是那个色调,稠稠的,液化的,听不到任何声响了,树枝也许还有叶子,细微的窸窣声也没有”。
爹重新那样躺着,用粗糙带刺的手抚摸我的肩膀,、手在说,崽娃子,瘦得像蚂蚱,靠近床的树枝也许还有叶子听到了,不远处的碾盘听到了,歪脖子槐树听到了,火晶柿子树听到了,桑树听到了……
碾场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将这些用心说给爹听,爹用手在我身上说的时候已到了涝池边的帽盔柿树旁,树梢在床的两侧,我用手摇了摇,树身在动,涝池周围的楮树、长在涝池中的柳树在动、爹用来推土的独木轮车在走动。
涝池里的柳树、村中的老皂角树、村北的古槐、我小时候摇过的椿树、雍河边知了父母临时吸取汁液的柿子树等都是很有意味的意象。至于原来浩阔的雍河岸边,更是树的绿色植物园:
河岸的林子密密匝匝的,杨树、枸树、槐树、椿树、软枣树、火晶柿子树、桐树,柳树、核桃树、楸树、榆树、桃树、梨树、桦树,还有不知道名字的树,相互交错,相互枝头搀依,荇草和芦苇长在河的浅水区。雍河两岸的树叶子回应了,桐树、柿子树、楸树、杨树、核桃树、枸树的声音是浑圆的,而柳树、槐树、桃树、椿树和芦苇、荇草的声音是悠长的。
可以看到,“树”就是“知了”父母的生存环境,代表着故乡那些与父母生活直接相关的风物。比如土地、比如房子、比如水源、比如空气,等等。随着环境的恶化,树的数量由多变少,由茂密变得稀疏;水分也由丰腴变得瘠薄,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生机与活力。包括树在内,后院、碾场、饲养室、涝池、窑洞等都是“我”生命和生活中对故乡最深切的记忆。都是我的灵魂之“床”。可是,它们都消失不见了。我们发现,“我”在灵魂时空,在故乡,已经没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没有了“根”,无所皈依。其实,岂止是“我”,我们的祖灵们也在外飘荡,找不到可以栖息的地方——因为新农村建设,许多外力的介入,土地被占,祖坟被迁拆,清明节的时候,城里人要祭奠先祖,还得到城市公路十字路口小心翼翼地烧纸上香——那种深度的感伤、焦灼、痛苦、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可想而知!小说中,作家把世界上消失的故土、故乡、故人等都异化成为“知了”的形式,曲情尽意,主要用来刻画中国乡村之被现代文明摧枯拉朽地改变,以及神魂分离之凄凉现状,借助梦靥这种非常态的形式,将这种深切的思考巧妙地传递了出来。
飞床、知了、树三个意象交错使用,就使得小说结构松散之中显紧凑,平凡之中又有传奇,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强化了小说的梦幻基调和氛围。
奇丽魔幻的语言
《知了》小说的语言很唯美,是一种奇丽魔幻的美。主要表现为既是一幅抽象的绘画小说,又是一篇音乐小说,一部命运交响曲。
(一)绘画小说 一幅时代抽象画
小说没有镜像清晰的故事情节,作家凭借超拔的想象力,用变幻无穷的画面推进情感,体现意象,彰显主题。
《知了》小说画面感极强。而且画面直接刻画时代,一幕幕充满想象力的画面,把历史嬗变,时代变迁,神魂剥离等的各种疼痛触目惊心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小说没有按照情节推进,几乎全部用画面推进。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一幅画面。“我”乘“床”故乡巡礼的过程中,许多镜头、画面虽然一闪而过,但是都是“我”生命中最雄厚的人文底色。从开篇就让人如在画中,呈现出一种抽象的错觉。“我似乎是睡在楼层里”,就是一个模糊的不很清晰的画面;听到知了叫声,也是一种懵懂的感觉。知了轰鸣声“似乎带有隐性,好像有巨大的知了蛹在地心走动、又像是巨大的犁铧,在深而有深的黑暗里游弋”,“巨大的蛹”、“在地心走动”,“巨大的犁铧,在黑暗里游弋”,想象力超凡,画面形象可感。从语言艺术来讲,都是抽象的画面,而且是跳跃式的,互不联系的画面。就像抽象的诗一样。
“我翻身”“爹和我光裸着”、“娘在箩面”、涝池张着嘴、扑簌簌落下的知了、正在被“车裂”的古槐、爹娘在地里劳作的场景、雍河岸边张开大口的窑洞、知了飞舞等等,都是瞬间镜头的撷取,一直是画面,好像是写实,却完全是写意。作家把那些画面用抽象的语言艺术组合起来。一个床上躺着,脑袋里翻江倒海,在狂乱地想象的作家跃然纸上。
如果说以前李喜林作品是水粉具象画,现在《知了》小说就是抽象画。作家好像手拿一把刷子,以思想为画笔,语言为染料,在打翻的颜料盘里胡乱涂抹,白描彩绘,墨线勾勒,意到笔随,处处都是画面,惊心的画面,像意识流一样漫漶流动的画面。泥沙俱下,却风起云涌;煞有介事却又模糊不清,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却蕴藉无穷的感觉。这些画面形成了各种形象,使得作品无迹可寻,大象无形。一定意义上,《知了》小说画面是MV,而不是定型的油画。又如:
我爬上墙,跳到壕里,轻飘飘下去,没有风与耳畔的磨擦声,又一个反弹跳到墙上,见月光灿灿爹正和二哥在推碾子,我帮着推,爹膀大腰圆,迈开大步像一匹壮驴,二哥比爹低一个头,我比二哥低一个头,爹走得快了,我在碾棍的外面一路小跑。娘在近旁箩面。
多么富于生活气息!多么的幸福诗意和浪漫!
我看见了村北头的古槐正陡然高耸,一个庞然大物将钢绳套在它的脖子上试图连根拔起,古槐庞大的根系在发力,与那个庞然大物拔河般撕扯,一忽儿古槐松动的根须在一轮博弈中站稳,一忽儿被庞然大物又拔高了些许,爹娘的手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拔扯正在我的肩膀上跟我一起给古槐加力。土地在颤栗,那些田鼠、野兔、蚯蚓在地下给古槐给力,古槐上扯网的蜘蛛给古槐给力。
这巨树和庞然大物就像魔幻的巨兽在争斗,显然完全是一种神性的张力。
床不断被撞击,床架子不是撞在石头般光滑的墙上,就是被撞在屋脊上,床显然很痛苦,但听不到呻吟声,很快我发现床架子已经没有了,一片床板似乎因为减轻重量,倏然飞起来。
床很痛苦?!这完全是人的感受么!作家通过画面的不断闪现、叠加,构成了层层立体的画面之网,整体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而且,看似毫无联系抽象的画面,但却有所关联,都是“我”过去的生活现场,都是我关于故乡的清晰记忆,都吸附在“乡愁”和“挽歌”的神魂主旨之上。应该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有的人事都是李喜林前期一些作品,诸如《生涩的火晶柿子》《乡村的诗意和浪漫》等中的场景,作家打破了艺术原来用写实再现小说语言的局限,将自己乡村书写的能力和话语暴力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熟稔的纷繁的艺术元素重新进行抽象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陌生化的小说语言形式,开创了新的语言艺术天地。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水深火热、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时代嬗变抽象画。
(二)音乐小说 一部命运交响曲
我们明显感觉到,《知了》是一部音乐小说。阅读中,文字里的音乐旋律贯穿始终,时而缓,时而急,时而动时而静,时而强时而弱,有静水潜流,有波涛汹涌,裹挟着寻根追魂的情感奔涌,形成了立体声音协奏曲,是回乡安魂曲,又是一首融汇了个体生命在历史前进的水流湍急中挣扎,彷徨,感伤、悲怆的命运交响曲。整个小说乐感很强。各部分基本都以音乐形式出现。小说名为《知了》,本身就奠定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一般说来,“知了”发出的声音都并不是怎么快乐的声音,甚至很悲苦。知了知了,好像什么都知道,全知全能,是一个变形的灵魂之音意象。
小说一开始就是声音,因为知了本身就是声音意象。父母在梦靥中出现了之后,声音听不到了。到后院就已经听不到了。正如小说所写:
夜还是那个色调,稠稠的,液化的,听不到任何声响了,树枝也许还有叶子,细微的窸窣声也没有。我对爹说话,我自己都听不见,只能说给心听,心再说给爹听。爹要坐起来,很费劲,我扶爹起来,似乎没有扶得起,爹重新那样躺着,用粗糙带刺的手抚摸我的肩膀,手在说,崽娃子,瘦得像蚂蚱,靠近床的树枝也许还有叶子听到了,不远处的碾盘听到了,歪脖子槐树听到了,火晶柿子树听到了,桑树听到了,矮土墙的地窨听到了,土墙外的大碾盘听到了。碾子在转动了,但没有声音。那一块地方三面靠土墙,一面靠深深的土壕,我爬上墙,跳到壕里,轻飘飘下去,没有风与耳畔的磨擦声,又一个反弹跳到墙上,见月光灿灿爹正和二哥在推碾子,我帮着推,爹膀大腰圆,迈开大步像一匹壮驴,二哥比爹低一个头,我比二哥低一个头,爹走得快了,我在碾棍的外面一路小跑。娘在近旁箩面,一个大蒲笸里面架二根光溜湢细棍,竹箩盛上碾碎的粮食,在二根细棍上面来回反夏,娘在箩面,手指间或阴柔的一弹,只是没有声音。
我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父亲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娘在涝池边洗衣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就用手在说话,用眼睛说话。作家用魔幻的手法,把音乐性的东西都转化为一种动态的东西。比如娘在涝池里洗衣服,声音就听不到了;用棒槌砸衣服,没有声音;娘在箩面,没有声音,弹出来的却只是音符;知了落在涝池里,也是无声无息。娘洗衣服,两个月亮也是以动态出现。月亮在水里,娘在水边,水里就两个月亮,一扭一扭地在说话——作家已经把音乐完全转化为一种情境性的东西。小说一直贯穿这些东西,到古槐下也是,雍河里也是,窑洞里也是……可以说小说是一篇有关声音的小说。
其实,知了的声音并不是小说主要想表现的意象,不是主旋律,知了也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音乐元素直接指向命运。人物的命运,故乡的命运,中国农村的命运!整个小说就是一曲音乐,一曲沉重的交响乐。起承转合,动静自如。突然间飞沙走石,突然间寂静无声。一会泥沙俱下,一会舒展悠扬。有张有弛,有声有色。感觉作家好像一直沉醉在音乐的想象力中,完全走火入入魔样狂奔,写出来的。读这个小说,不由得想到了贝多芬的《悲怆》的曲子。最后,“我”给“知了”爹娘说:河边有烤肉架子!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悲凉、悲伤,再加上泪光画面的叠加,和音乐连接在一切,让人极度的震撼!
现代“乡愁”的创新表达
乡愁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生态,也是人们永远无法克服的情感指向。在中国,对中国农村现状关注的作家很多,写乡愁的也有,但大多都是从正面切入。这篇小说却独出机杼,选择了“梦靥”形式,从而把天地连接、阴阳打通,把生死超越了。
众所周知,梦是现实的折射。梦境和梦靥是作家创作的核心地段,可以直达人心。对好作家来说,作家要尽量用作品把人的内心、灵魂唤醒,振聋发聩。梦一般都很惊心。从梦境里出来,人的心往往通通直跳。我们知道,在生活常理上,就不可能有飞起的床,但是在梦境中,可以把小说的长度、宽度、维度、多角度等都进行艺术地实现。再加上记忆叠加东西的共同作用,小说格局和气象就有可能走向开阔地带。可以说,作家在梦境中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般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小说,要求有一种生活的逻辑,表象上不能有变形、夸张等,但现代性写作就可以。这就是我们都公认的:作家一般都是精神疾患者。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作家正常了就没有文学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已经成为经典就是证明。无独有偶,作家残雪也写过一篇《与人为邻》(《上海文学》2016年六月号),也是以“喜鹊”的目光巡礼身边的人性嬗变和社会的变迁。不过,残雪选择了一个相对静止的“喜鹊巢”意象,写得比较明亮,写阳光下的罪恶;而《知了》选择运动着的“飞床”意象,写夜幕下的梦靥,直接就是一个梦靥。两个作家同时用非常态的方式在把握时代的脉搏,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知了》小说很短,但是结构相当宏大。不仅声音作为小说审美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渗透在字里行间,画面更增添了小说的兴味,另,“知了”只是作品的壳,而正在被湮灭的农耕文明才是作家真正要彰显的内里呢!此外,知了还叫蝉,蝉通禅,这就自然使小说带上了一种神性的东西,和佛有联系。小说的哲学意味也很浓厚,写存在中的存在,存在之上的存在。结尾更是充分贯彻李喜林近年对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写作的探索理念:好小说必须首先要有文学地理,其次其主旨必须指向虚无和模糊、多元。比如古槐这个意象,我们知道,古槐是村魂。村魂往往与树连接,树总是根植于大地,而象征着“村魂”的古槐竟然也被连根拔起,说明本篇小说直接就是乡土社会的一曲哀歌、挽歌。看惯了平铺直叙的小说,一定意义上对那些只讲故事,没有思想的作品敬而远之,李喜林却剑走偏锋,以“梦靥”进入,直接与当下乡村题材小说写作的粗鄙化、简单化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精气神重新振作了起来。
李喜林以前写的小说我都系统读过。最能代表他水平的就是《映山红》和《生涩的火晶柿子》。前期作品比较清新,主要偏重于对人物内心、灵魂的裸裎。《知了》这个小说完全与李喜林以前写作风格大相径庭。相比于以往,水深火热的飘逸之中更显沉重,可以称为颠覆性、全新的建构性作品。我经常把作家写作分为两类:匍匐式和眺望式,这篇小说直接是“飞起来的小说”。一开始就是“飞床”。虽然短,但是把作家之小说创作观点、意识、理解全部凸显了出来。以前没有读过李喜林小说的理解起来可能不容易,但是这个小说完全可以单独成篇。
总而言之,这篇小说手法新颖,意义非凡,质量上乘,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让人惊喜,耐人寻味。(作者 孙新峰)
作者介绍:孙新峰,1972年生,陕西洛南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硕导。陕西省百名年文学艺术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