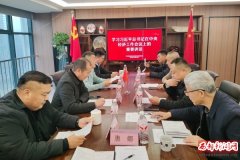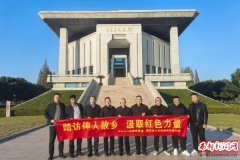肖老师母亲欧阳明玺(中)
在编《民族文化结构论》这本集子的时候,常常想起我的母亲,要是她活着,今年已是80岁整。二十八年前弃我而去,她52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
几十年来,思念有如流不断的涧水,剪不断的云翳。思念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而在研究学问时,如此执拗地、排解不开地想起她,还是头一次。
好不惑然。
半岁丧父,亦无兄弟姐妹,母亲终生守寡,将我拉扯大。我于她,她于我,都是唯一的、独有的。她携着我,我搀着她,脚印交织在人生路上。
母亲大半生任教于中学,晚年调入图书馆,一直住在单位的单身房间。我初中以前,被寄放在外婆身边,她每周回来看我。高中起我在市郊一所学校住宿,每周必定回去看她。

有次她对我说:下星期有事不能回来了,不要想她。那分外的温存,使我过敏地感到这是要扔下我远行,竟然怀着少年人不该有的悲哀和惶惑,悄悄跟在母亲后面足有一个钟点,直到看见她确实进了学校的大门,而不是去了车站,才 脚踏实地踅回。
又有一个星期天,因为下雨我留在学校没回家。雨停,时已过午,想不到她让一位学生步行15华里来看我。我便又步行15华里回去,让她确证儿子的安然无恙。那时中学生很少有自行车,我们用脚板一步一步丈量感情。
每一次离别,无论短长,母子都要和孑然一身的孤独作一次搏斗。大约从那时候起,中国古典文学中描绘“倚门倚闾”的诗文书画,便一遍一遍地感动着我。
实在也苦了她。因着浓冽的爱不能不压抑自己的爱。
母亲是知识女性。整整四大本相册,记录着她挥斥方遒的激情的青年时代。
“一二·九”运动在北京的有轨电车上散发传单。
搂着卢沟桥的石狮子大笑。六位女同学平卧雪地,摆成六角的冰花。
在教会学校和美国神父面对面论辩……
她并不封建,在自己的历史论文和历史剧中,一再为被封建文化窒息的中国女性呼吁。但在28岁守寡之后却没有重新组织家庭,尽管有人撮合,尽管外婆催促。我想那是为了我。成年之后,我才加倍痛切地感受到母亲这样子生活的孤寂。孤灯冷月下的24年,八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容易的么?每当她听唱片,便有如一颗孤寂的心在自言自语。囿于当时的文化氛围,加之我不是女儿,上大学后几番欲言而未启齿。
母亲的感情生活中为儿子的自戕,使我终生内疚。
母子之间的爱都无私。
就连母爱,她也不能不斟酌着、节制着表露。
作为寡母,她必须同时具有父之尊、师之严、友之诤。
对我的功课近乎残酷的督查,每每使外婆暗自流泪。至今想来,仍然引起甜蜜的战栗。我甚至很过她,又终于懂得能够从小接受大松博文式的教练,是我的造化。那远低于家庭经济水平的简朴要求使我简朴,那不完成计划不能睡觉的训令使我勤奋。铁器是在铁砧上锻打出来的,若要一位寡母如此来锤打自己的独子心里是怎样的滋味?
直到今天,母亲严厉的目光,仍在天宇中监测着我,催我奋力奋进,催我自思自审。
由不惑而届知命,母亲有了一点变化。先是稍稍超脱了繁忙的学校行政,而后又稍稍超脱了省图书馆的机关事务,重新拣起历史专业,开始了女性系列历史剧的写作:《嫘祖》《班昭》、《李清照》、《赵飞燕》《武则天》……直到《秋瑾》。有的演出了,更多的存于箧底。《秋瑾》只写了第一场,便和一封给我而未发出的信,一块掰开吃了一半的点心,永远留在了桌上。——第二天,她被死神遽然劫持,因为脑溢血在省人代会发言后倒下。从此长卧于江南的红土地中。
转向历史,对母亲来说,也许是一种人生的沉凝,也许是一种感情的蒸腾,我不得而知。也许阅历总要使人皈依土地,皈依文化土壤。
也恰恰是由不惑而届知命,我的兴趣悄悄地发生转移,开始钟情于历史文化。内中原因也不得而知。分明不是有意识要接续母亲在52岁时嘎然中断的工作,只能说是生命自然运行的结果了。
生命来源于母体。精神根植于历史和现实既在的文明成果。每个人都从脚下的土地上起步,经历了青春的翱翔,总有一天要重新降落在土地上。尽管那是另一块土地,尽管那里有另一番风致。
自从剪断脐带,我和母亲的联系由血肉的直接交溶转而为语言和文字的传递,为眼的流盼,为心的感应。50多年中,我们日甚一日娴熟地在各种有声和无声的频道中联系,哪怕地隔千里,哪怕分隔于两个世界,一直相依为命。
有时我想,母亲之于我,已经是一种传统,一种标尺,一种基座,一种象征。有了喜悦,走了弯路,面临抉择,很自然地就和冥冥中的她对话。那往往是以历史和人生的基座在检视自己。
真应了郭沫若早年的名句:“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母与子这两个“一”,占有着对方的“一切”。母与子这两个“一切”,凝结为对方的“一”。
近30年了,回江南扫墓的机会那么少,我几乎没有正式祭奠过她,也没有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这都是儿子的罪过。
我的母亲,愿这本涉及历史和文化土壤的书,能寄给你些许的慰藉,能赎回我如山的歉疚。(文/肖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