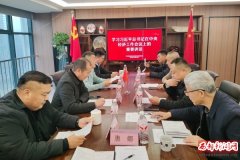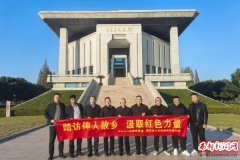流年如风,这已是我当西安居民半个多世纪的第5次搬家。
最早住在城墙圈里,东大街老陕西日报宿舍,两人一间,先后同舍的三位同事,成为古都赐我的第一批朋友。后来结婚了,换到西楼一间房,一家三口人均不到5平米。十几平米不但住下了一家人,还大床小柜、书桌书架齐全。有次竟然在脚地上支起折迭方桌,请“笔耕”文学评论组的10来个人吃了一桌饭---当然蒸炒煮烹是在走廊里完成的。记得杜鹏程、贾平凹、路遥、王愚诸位“大鳄”,都屈尊赏光过这方寸之地,寒舍于是响起鸿儒们的阔论。东大街那时算是我的前院,钟楼是我的门楼,每天傍晚携妇将雏散步一趟,固定的路线是:徜徉于东大街,到钟楼打回头。

再后来,搬到了文艺路北口,80多平米的小三室,人均达到了20多平米。有幸的是,开窗依然可见城墙,与碑林和董仲舒墓隔墙感应,离古城的城标--南门广场也只一箭之地,文气和古趣是越发的浓了。于是全家决定把南门广场收入彀中,定为家庭前院。散步路线改由沿护城河西行300米,绕广场一周打道回府。妻子在这时评上教授,儿子在这时读完大学。但很快,一幢幢楼房南北挟持,周边愈来愈金碧辉煌,小楼象误闯宫庭宴会的灰姑娘,面无阳光。只有下午4、5点钟,对面楼上玻璃窗能将些许“二手阳光”反射到室内。无奈中,命名此屋为“谷斋”,署在这一时期所有文章之后。想不到的是,15年后,我竟然被聘为文艺路整体改造工程策划书的总顾问,小楼迟早要拆迁,能为老宅老友尽一份心,也算天遂人愿。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正为着结识了一批新朋友而高兴呢,想不到老朋友又纷纷在这里露面,不定从公园的那条小径上便迎面走了过来。“哈,咋来西边了?”“搬过来了!”西北大学的、出版系统的、文界书界画界艺界的朋友们,成建制地搬过来了,巴山深处镇巴县的老友也搬来享儿子的福了。城市的拓展,发出竹笋爆出土地的响动,那是春天才有的声音。每个搬家的人、每套新房背后,都有一段人生故事、一段都市故事,都是生存状态改善的一个信号,一个音符。她们组成了活力充盈的都市交响曲。于是,我在央视“精彩中国”节目中,有了这么一段说道西京的话:西安也许正在形成三个文化生存圈,一个是古城墙内外典雅的传统文化生存圈,一个是二环内外活跃的现代文化生存圈,一个是秦岭环山路内外休闲的后现代文化生存圈。可不是这样!
人搬了家,书也搬了家。在我家,书从来比人的待遇高,人只占两米见方的一张床,书们却满满当当占去了四个房间的24个书架---她们己经换妆七次,七代书架,由自制的砖垒木架板,到泱泱君子风的落地玻璃柜。感谢陕西电视台摄制了专题片《肖云儒的七代书架》,将书们的迁徒纪实下来,见证了西京历史。
人和书这么一搬动,神也有点想搬家了。打50年前来西京,头几年适应北方生活,而后便是10载文革动乱,20载中年拼搏,成天忙得把时间掰开来用,竟然少有兴致品味自己居住的这个都市。花甲之后,当我从绑架了自己大半生的理性思辩中抬起昏聩的头,蓦然回眸,西京竟是如此的百媚俱生!我这才开始认真阅读、品尝这座城,继而解读、传播这座城,在人和城的顾盼中,建立起信任和默契,从此乐不思蜀。于是在各种媒体上说道西京,说兵马俑华清池,说古城墙大雁塔,说终南山大明宫,说芙蓉园不夜城高新区经开区飞机城航天城未央宫广运潭楼观台书院门骡马市民乐园东汤峪,当然也说道西京的文化局限和精神缺失,引发掌声也引发骂声。怕是只有爱只有关切,才会如此喋喋不休、如此挑剔吧?
说就说说而已吧,不,还不解馋。还厚着脸皮掺乎到旅游、城建、策划的队列中去,假模假势干将起来。还别说,一卷起袖子便弄假成真了,干得煞有介事,干得乐在其中,越干和西京城越黏乎。
光阴就这样在搬家中匆匆走过。50年、18000多天,我与西京城就这样耳鬓撕磨,就这样狗皮褥子没反正,就这样共着始终。(2010年11月27日于西安不散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