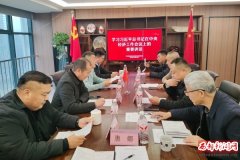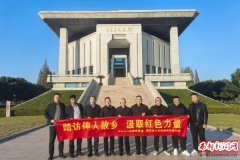商先生是能写各种文体的,他的一篇散文《刻在心头的微笑》(发在《西安晚报》上),大概距今有三十多年了,却仍然“刻在我的心头”。一个下雪天,薄冰覆盖着路面,很滑。商先生正在过马路,一辆公共车开了过来。这时,要么商先生加快步伐,要么公共车停下来。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啊!加快步伐意味着可能摔倒,不加快步伐意味着可能被撞。生活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商先生是幸运的——公共车停了下来,车门的窗户中露出司机的半个身子和一张微笑的脸——那意思分明在说,不着急。慢慢走。

其实一言以敝之,杂文家的被冷落,折射出来的现实是,这个时代不喜欢杂文。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其中有周谷城、罗稷南等人。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对文化人士的担忧。罗稷南瞅了个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大胆的设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从毛泽东的回答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写杂文是需要勇气的。在另外一次对话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杂文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已经在中国的杂文界有了不小影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严秀)曾称赞他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一大批中青年杂文作者中最引入注目的三位之一。从那时开始,他的文章不但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香港《大公报》、《西安晚报》,以及《文汇月刊》、《新观察》、《随笔》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而且还被数十种权威选本收入。退休以后,他开始致力于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新书送你,其中就包括近200万言、四卷本的《商子雍文集》。我曾多次有幸与商先生一起用餐,席间不免会听到人们对他的赞美,其中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看着您的文章长大的。”
一个人的文章能在一个人的心中存留很长时间,一定是有分量的,也是有质量的,否则,他不会“看着长大”。饭菜都会换着吃,奶粉也要进口的,精神食粮更是要精心挑拣,何况商先生的文章并不是中学课本,非得要在规定的时间读它!近年来,平面媒体的文章要求正面报道的刚性愈来愈强,杂文也就愈来愈难写。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杂文。当然,他也感到了杂文在平面媒体上的空间在缩小,不得已在新浪开了博客。我与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博客的。但我是登书法图片,他是登杂文,许多年下来,他的点击率已相当可观。可以说,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些挤压弱势群体的事件,几乎都可以听见商先生的声音。博友们对他的留言多为“尊敬”“致礼”“保重”等,字里行间不无由衷的关怀和钦佩,对他敢于批判的勇气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称道,也有博友送他“时代良心”等评语。

商先生是那种放得开的杂文家。写文章总有“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感,大有东吴抗曹的风度——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做人上,也属大气型的,同事朋友间开玩笑似乎说啥都行,从不会为某句过头话和错话而动容,自嘲和他嘲都充满了智慧。有一次朋友间开玩笑,说他能演毛泽东。他笑着说,这样的好事一定当仁不让,不过,扮演张玉凤的演员须得自己来选。有一次,与陈忠实一起乘车。陈忠实说,子雍多大了?商先生说,与胡锦涛同岁。陈忠实说,我不与胡锦涛同岁,我与子雍同岁。

我们见他辛苦,就劝他封笔。他说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尤其要发声。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明哲保身,持默守静,于社会于自己都是一种危险的选择。鲁迅说,要做韧的战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说的吧。地震有名言:微弱的声音胜过无声。发声不一定会有希望,但不发声则绝对没有希望!(文/马治权)
201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