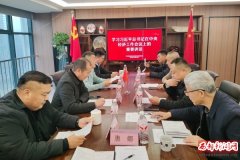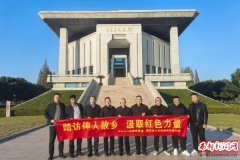那些刻在骨子里的秦腔印记
---长篇小说《乐人》后记
记忆中我好像四五岁就被父亲带着穿插在秦腔各种戏曲舞台,只要大幕拉开我就会乖乖坐在父亲乐队中的板胡盒子上,每天耳闻目染各种民族乐器及秦腔戏曲的唱腔。那时总是充满了好奇,总爱模仿那些阿姨走台步,唱戏词,摆布木偶。谈不上喜欢,但也不反感,只是觉得好玩,彻底对秦腔反感和逃离是在我10岁那年,父亲因工作原因去了当地一所戏校任教,也许父亲内心有一丝女承父业的打算吧!我被带到了戏校,记得父亲把自己一个月75元的工资给了一位要去西安出差的老师,说回来为我带一把琵琶准备让我学习,但在这期间我被学校的一位教唱腔的老师拉去了练功房,开始和那些比我年长一两岁的哥哥姐姐一起练功,练声。
有次下课路过教师宿舍,我听见了一种美妙的旋律,如一幅流动的画卷,仰扬顿挫充满了美感,曲调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随着声音不由自主站在一间教师宿舍的门口,看着屋里的阿姨手指拿着纤细的小棍娴熟地敲击着如桌子般的乐器,我偷偷躲在一旁边听边看。当然最后被阿姨叫了进去,她告诉我这乐器叫扬琴,问我喜不喜欢,如果喜欢她可以教我,当时就让我找父亲去说,当我告诉父亲我想学扬琴时,父亲苦笑了一下说:“今天你们教唱腔的毛老师还说让你去学演员,说你来了一周功夫都赶上其他同学了。”“对了,毛老师她还说我不学演员可惜了,夸我长得漂亮!”我笑着回复父亲。那时我看父亲有点茫然,犹豫着不知道让我走哪条路了……
接下来的日子如魔鬼训练营一般,我早上必须5:30起床去练声,然后回来洗漱吃早饭,接下来就是两个多小时的基本功训练,结束后我还要被父亲训斥着练习二胡(自己教乐器不用付学费),一有错音就上手打我的手指,还要我每天按时去学习文化课,整整一个月我每天都在那种强压下循环,我终于在父亲又一次的呵斥中爆发了:“我要回家上学,永远都不再触碰二胡了,我讨厌秦腔!太难听了!”我哭着对父亲说要回家,要回去上学。也就是从那时起30多年来从没有再摸过父亲的二胡,一听秦腔唱腔就逃到一边。我以为我这一生与秦腔与民乐再不会有交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也经常听父亲讲我熟悉的那些叔叔阿姨的现状,依旧艰难地穿梭在乡村的各个红白喜事上。仍然坚持传承即将失落的传统戏曲文化和关中的民俗风情。他经常对我说:“当年你多亏没学戏,要不然现在也还在四处奔波讨生活……”
从小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一生热爱文学,擅长多种乐器,因命运的多舛始终没能端上铁饭碗,但他始终热爱生活,农闲时经常发表一些散文、诗歌。小时候经常听他给身旁的文友讲述鲁迅、路遥等文学名家的作品,剖析当下的社会形态,我也特别爱听,也爱翻看父亲仅有的几本书籍,也许就是那时他为我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上初中后也经常爱写一些诗歌,爱思考人生。但走出校园后因为工作、生活就再也没时间去触碰文字,但脑子里经常会闪现出那些记忆中的戏曲元素。也经常想如果有一天时间允许我一定要把父亲这一批底层民间乐人的喜怒哀乐给记录下来。
和父亲一样的一批音乐人被命运抛向“乡村乐人”的行列,他们终日忙于乡村婚丧嫁娶的“顾事”。他们的灵魂拖着沉重的翅膀飞翔,依旧整日沉浸在“喜怒哀乐”的旋律中过生活……他们经历着时代的变迁,经历着戏曲从繁荣走向了低谷,也遭遇了罕见的衰落,但依旧热爱着他们传承的文化信仰。我也经常会听到父亲讲述他身边那些命运坎坷的叔叔和阿姨的故事,感叹着命运对他们的不公!我一直在想为他们这群人做点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疫情期间我和父亲去看望和他一起在剧团乐队的好友,也是一位当年考上海音乐学院全国排名第二的叔叔(全国只录一名),他突发脑梗从南方一所民办大学被送了回来,拉了一辈子二胡,创建了学校民乐系。最后却因突发的病情手再也触碰不了琴弦,那一刻更是让我下定决心尽快动手,在创作期间我经常给他打电话问询当年的一些情况,他很感动,说终于有人关注到他们这一群人了,让我完成书稿后第一时间送他一本,但是小说出版的过程繁琐,他也最终没有等到小说的出版就离开了人世……这也是我最感到遗憾和心痛的一件事!
也许秦腔的曲牌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才能理解它的沧桑和悲壮,它能够一瞬间唤起人们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和对故土的眷恋。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曲调,我也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秦腔音乐的精髓。创作期间我的房间里整天循环播放着各种秦腔板胡、二胡的曲牌,还有一些经典的秦腔唱段,那一刻我随着文中的人物一起感受着他们喜悦和撕心裂肺的伤痛,眼里时常含着泪花随着乐曲一起飞扬……我还没能感受出他们的悲苦更深一层的意义,只是记忆中的那些不能忘记的人和曲,突然在一瞬间还原出他们的青春,走进他们的生活,三十多年没张口的唱词,也清晰地被我吼了出来,台步、身段一招一式又一次验证了我曾经练习过……
也许这就是藏在骨子里的记忆,到一定的时候它会出来直接把你唤醒,使得自己不无郑重地拿起了手中的笔,为那些所有的底层的民间艺人,在悲苦的人生中依旧热爱、传承着民族文化的人写下了这部饱含着他们血泪真情的文本,为乡村乐人苦难命运的沉浮,和给那些无助的底层人民一点温暖和光。创作期间因为孩子还在高中阶段,晚上我还要操心她的学习和生活,我基本都是早上5点多起来给孩子准备好早餐,孩子去学校后我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自我的空间,随着人物的转换而转换,有时连坐5个多小时不动,腿有时僵硬到不能活动。记得我妈说我,你要是当年上学期间有着这样的学习精神,估计你北大都能考上!我只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内心总有一股无形的动力不时地在催促着我!我知道那是他们想借助我笔下的人物为生活中的苦难呐喊、为自己舔舐伤口……
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阎纲先生读完部分章节赞不绝口,立即为“乐人”提写了书名及推荐语:“我上初中时,学会了打板,在自乐班司鼓,也为村人过事吹吹打打,日后写过一篇文章《戏曲送我走上人生舞台》。今读郑曼长篇小说《乐人》,一惊,她三十多年没有张口,深藏在骨子里的记忆唤醒了她,一下子吼了出来,连同台步的一招一式。三十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深入到乐人群体的灵魂,她写他们,我等如何比得!
她第十章写采儿,让人叫绝,唱戏给她黄金裹身,黄金异化她一文不值,变成疯子。这是三代乐人七十年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本,是关中风情多姿多彩旳演示,是为底层乐人在悲苦中依旧热爱、传承民族文化饱含血泪真情的文本。---它才是“人生舞台”灯塔般的风向标!
熟悉的陌生人,余味曲包。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欲罢不能,改编电影和电视剧恰逢其时。阎纲”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春林先生及著名作家杨焕亭先生推介作序和评论,让《乐人》平添一份“出世”前的自信,在此一并感谢三位老师认真的审读、点评和提名!也再次感谢所有关注助推着《乐人》这一部作品顺利出版的朋友们!
2024年.3月.13日于西咸
作者简介:郑曼,女,陕西礼泉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海外文摘》《天津文学》《星星诗刊》及《延河》上半月刊《散文选刊》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诗歌200多首、散文数十篇,其中散文《六爷》荣获“2021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诗歌《今夜,我在想你》荣获“云上七夕诗会最浪漫诗歌大赛”诗歌奖第一名,由延安市文旅局,作家报社共同组织的“百年辉煌.回忘延安”诗歌大赛中组诗《走进延安》荣获大赛优秀奖。《你说,你是援藏干部》被人民数字网、新华社客户端转载浏览点击阅读量达到115.2万次。出版诗集《一株玫瑰》上下册及长篇小说《乐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