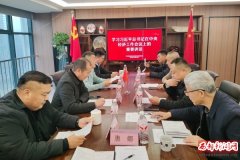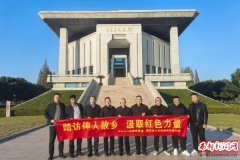贾平凹(图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贾平凹,陕西丹凤人,生于1952年。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2006年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
如实记录时代
我的文学创作接近30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我都参与了,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致上我都知道。时间虽然漫长,但经常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就是30年,最初接触文坛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现在也经常感觉大学才毕业就几天——老是有这种感觉。
当时,我刚从农村出来,吃不饱饭,我深深了解生活的艰难。
在我所经历的生命过程中,30年来,国家在富强,人民在富裕。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这30年是振兴的、蓬勃向上的;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30年是人性充分展露的时期。文学和政治、经济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文学主要是关注人性的问题。这30年有令人亢奋、激动的东西,但是也有让人痛苦、挣扎、无奈的东西。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黄河在陕西里的一段,河里面的土特别厚,黄河水在那里流动的时候就好像不动,一看就是泥土在流,看上去几乎没水。这个大时代,就好像我在黄河边看到的这种情况,一切都在搅合着走。中国好多事情往往是只可做,不可说,有的事是只可说,不可做,糊里糊涂的。
从文化角度讲,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应该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很丰富,提供的想象空间特别大,素材也很多。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一部分活得很好,一部分也活得很不好。我举个例子,我是从农村来的,创作也一直写农村。
大量的农村,尤其是西北的农村,走城市化道路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这个过程很长,走这个道路的过程中要牺牲一代或者两代农民的利益。当这种痛苦、无奈聚集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它会占领一个人生命的全部过程。所以这个时代是让人特别激动,也是让人落魄的,正好把人性的各个层面都展现出来了。
我记得我年轻时谈恋爱,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售货员。当时介绍人就说这个女的条件有多好,这个女的每天要喝半斤牛奶。当时这半斤牛奶就把我吓坏了,就再也不敢谈恋爱了。当时我刚毕业,一个月才领39块钱,我们那里没有牛奶也没有羊奶。当时就只有小孩哭闹的时候才喝牛奶,她都要喝半斤牛奶,所以就没有同意。
这是琢磨不透的一个时代,有人看你不行,但是你一夜之间就可以爆发,又可以一夜穷亡,人性的大暴露通过各个层面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能在这个时代生存是很幸运的。那么,文学在这个时代又该怎么表现呢?我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我除了创作还喜欢收藏,在家中收藏了大量的东西,我收藏的主要是汉代的陶罐。汉代在中国是一个强盛的时期,我现在收藏的这些陶器,不是很大气,是汉代那些人随便做的,可以想象那时人们精神面貌是怎么样的。清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但他们的器物做得很精细,比如景泰蓝的扁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不是说这个时代好,那个时代就不好。一切回头看,是看得最清楚的。吃饱饭和受饥饿的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有钱人和没钱人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那就不如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在作品中把这个时代真实的一面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改变文学观
前些年我教了3年的研究生,我没有教他们什么东西,就是灌输给他们怎么样去改变文学观。我觉得文学观对中国作家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如果现在还按照上世纪50年代那种写法和思维精神来的话,也许就没人看了。
现在往往发展成用一种理念写作,就是要求时代精神,强调作品的精神性,一般的作家或写作者认为小说的精神性就是人对生命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理解。现在文学界都讲世界性、现代意识,我觉得就是一种朴实意识。为什么要去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东西,因为西方对人的关怀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文学观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涉及作家的要求,更有读者的要求,要结合起来,才能改造文学观。我举个例子,以前放的电视剧《渴望》很红,红的原因是大家很认同里面那个叫刘惠芳的形象,这种善良妇女永远都会受到认同。我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叫《高兴》,主要人物是刘高兴,写的就是农村青年的一种新形象。人们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河尚,基本上是按照一个人的四个层面来写的,当时我写《高兴》时,也想把刘高兴作为现在农民的各个方面来写,但是作品发表以后,很多读者反映杏胡写得比较生动,刘高兴好像不像农民。当时我就回答,这是你脑子里面一直装着的农民形象,195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愚昧的、傻傻的、不卫生的。而刘高兴刚好是现在时代的农民形象,不像以前传统的农民的形象。现在农村的青年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生,到城里来,看不出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杏胡是以前的形象,读者马上就认同了,刘高兴就不认同了,这就是读者在阅读上面还有一个文学观念没有改变的问题。
一部作品不在于写得多生动,情节多吸引人,关键在于给读者的启发有多少,能给读者留下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读作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部作品能给我多少感悟,这种感悟是否形象、强烈,能否让我为之一振、过目不忘,这是我看作品最看重的一点。另外就是这部作品有没有生活实感的东西,它是从生活中、启悟中产生的,还是从别的事上得到一种启发或者一种观念的写作?它是从生活启悟中产生还是从观念上进行写作,是不是用技术性东西来掩饰的一种编造?文学可以映射出很多东西,所以我看作品主要就是看里面有没有实感,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东西。
作为一个现代的作家,首先要关注这个社会,要了解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况,如果你不关心他们,你写的作品同样没有人关心。还有一种作家,时间长了以后,刚开始时靠他的积累写一些东西,时间长了就变成职业性了,就靠自己的技巧性来写作,但是读完以后,震撼性不强,这就是缺乏生活实感。前几天我也和评论家谢有顺谈到“作家写油了”的问题,在书画界里面,一直在强调由熟到生的问题,一直强调要生,但是文学很少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文学也千万不要写“油”了。
文学要有民族特色
这些年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在复制西方,经济、建筑、文学上都是这样。从西安到东莞,建筑都是差不多的。而文学也是这样,这几十年把西方各种流派复制了一遍。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又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子。1985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学思维就开始改变了,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同时也导致了很多读者的阅读认可程度降低了。许多知名的先锋作家后期的作品也明显改变了。
在199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过一些关于云彩与阳光的观念。没坐过飞机以前觉得天上只有云彩,而坐上飞机之后往下看,飞机下面全是云彩,而云彩上面全是阳光。当时我就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学,它的最高境界还是要到穿过云层看到阳光,西方的文学就是穿过这个云层到阳光层面。我觉得一个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它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经验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云朵一样,这个云朵下雨,那朵云下冰雹。所有的阳光都会穿过云层,所以作品要达到阳光的境界,这是最终目标,至于从哪个云彩下面穿过,那是你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自己要有民族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现代思想、思路以及新的文学观。最近几年,在这个方面,很多作家做得也非常好,但是更多的人不太注意这种东西。现在的作家,接触面很广,不像我当年搞创作的时候起点很低,文学头脑也很薄弱,看不到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的文学青年,最开始接触的就是西方文学,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拥有太多复制性的东西也是不行的,追逐人家东西,一般读者接受不了。一定要写出中国的特色,不要去写外国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水平高的,写的作品就好,反映水平低的,写的作品就低。所以要强调民族性,就拿我个人的创作就是这样追求的,达到达不到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要有这种意识。
文字饱满才能有所承载
文学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古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人的三个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觉得,现在的文学达到了第二个层次,文学作品的最高层次是第三境界。
很多评论家强调精神性、境界性,其实还是强调第二层次,很多作家故意在作品里写对社会的批判,与政治世界的对应,或者是一些夸张、变形、暴力的东西,虽然这是创作很重要的东西,但我觉得作品里老是强调这个,还是停留在第二个阶段。在目前状况下来看,写得优秀的作品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过去有一句话叫作“大人小心,圣人庸行”,我觉得作品应该达到这种境界,虽然表面上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文字后面透出了评论家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作家,要有扎实的写实功底,任何现代文学,不管是什么流派,都是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上,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小说很虚浮,其实就是写实功底不够。尤其是读一些作品片段的时候,学的是西方故事的构造法。中国小说是现实的,西方小说是渲染、夸张的,这些风格显得非常有才气。但是一要求写实景,作家们就马上觉得写不下去了,就显得很虚假,这就是暴露了写实的功底不佳,现实主义的小说,写实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写实功底扎实了,其他的表现手法才能运用好。
再就是写文章要写饱满,小说有它基本的东西,很多意识,都起源于实用性的东西,但到一定程度后就玄乎了。就拿书法来说,书法本来是是非常实用的,现在说起书法时用的词汇玄而又玄,不知道书法是什么东西。文学也是这样,有时弄得很玄乎,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就像走路一样,先迈出左腿,再有右胳膊放在后面,这样反复强调几次,反而不会走路了。
所以,我觉得小说有它最基本的东西,有些大作家写的作品就是写生活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两个画面,因为他把特定环境的人和事写得特别饱满,作品所要求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就像一个人一样,长得高高大大的,身体非常健康,他就可以承载很多东西,可以背负很多东西;如果本身是一个病恹恹的残疾人,就不能指望他来背负多少东西,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
《红楼梦》也是这样,它就是写一个大观园,把大观园里的人和事写得很饱满,没有涉及当时朝廷、社会的事情,没有映射、对应的事物。从人和事里面就能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赋予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从音律研究来讲,可以这样那样,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讲,首先要把这文章写得饱满。
佛教里面有一个理论,强调生命的平等和灵魂大小的问题,也有讲到生命圆满的问题。如果做人,就要好好活,如果做树,这树有十丈高就要长到十丈高,要是达不到,就说明生命不圆满。
创作也是一样的,要把人和物都写得圆满、饱满,写饱满以后精神才能进去,才能承载许多东西,如果写不饱满就无法承载那些东西。(文/贾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