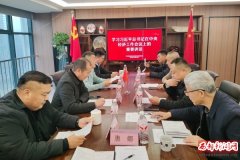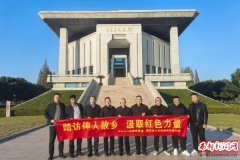2013年5月底应邀到香港参加有关《群书治要》的学术会议,完事后在深圳被失散30年的老同学马涛留住,从此,我和深圳的缘分开始了。
香港是一个拘谨有序的地方,再加上参加会议的都是些陌生的有修为的人,所以,会场的气氛有些人为制造的过分和谐。那几天,我周围的人个个都文质彬彬,谦恭有礼,见面鞠躬问安。而我这个来自西北素来粗放的人,有点像野猫跑进白天鹅堆里那样无所适从,那样惶惶不安。别人见我都谦卑地鞠躬,而我却腆着肚子不知还礼。别人都烟酒不沾,杯水素食,而我却被思念烟酒的情节纠缠着,寝食难安。所以,不等会议结束,我就急不可耐地逃离香港,联络了我的同学马涛。马涛来到口岸接我,我们一见面,来不及握手,就各自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
马涛也不是一个平凡角色,他是深圳阔太集团的大掌柜,手下也是有千十号人马,平时也是背着双手吆五喝六的。那天,我们就像两个真正的陕西农民一样,蹲在自家的土地上,呼吸着无拘无束的空气,望着广场上那些同我一样粗放的人流大声地说了一顿粗话,狠狠地在地上丢了几个烟头。
马涛是我的同学中最传奇的一个。他是大才子,又杀过人,坐过监狱,后来又成为名声远播的大老板。他的经历是最叫人惊心动魄的。
我和马涛都生长在陕西省礼泉县。礼泉是中国最早一批建县制的地方,只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礼泉,而叫谷口。谷口是西周和秦国的中心地区,是周人和秦人的正宗。所以,马涛和我都有着周人和秦人的长相和性格,有周人遗传的道义,也有秦人遗传的孔武。马涛身材高挑,长眉细目,粗狂中显露着文气。他如果站在西安兵马俑的军阵中,是很难区分他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件文物的。
我和马涛在罗湖口岸的广场过足烟瘾和乡音的嘴瘾,马涛开过来他的奔驰,我也挺起腰身,做一个学者的样子。我们进入深圳市区,再次进入我们各自的角色。
我那天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马涛拉着我直接到他的一个朋友老孙给孙子办的满月宴会上。老孙是浙江人,而他的宴会上却口音杂乱,东北的、西南的、西北的,广东当地的。马涛说,这就是深圳,一个庞大的移民城市。而这些现在纷纷当爷爷了人,就是第一批来深圳的打工者。我看着这些头布华发的人,算了算,从当年有人在这里画个圈开始,已经30多年了,30年前这些20岁出头的小年轻,如今也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龄了。我是一个多事的人,几十年的记者习惯使我喜欢对别人发问,而且喜欢问一些容易让人伤感的事情。那天,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哪里人?你还回故乡去吗?你为什么不老死在深圳?把这里作为自己安葬之所?”那天,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不是深圳人,我要回家去,我要埋在故乡的泥土中”。甚至连八九岁的童子都告诉我,她是外地人,不是深圳人。
一个人身处他乡,整日被思乡的情绪牵挂着,在文化和地理上无法认同,也是一件煎熬人的事情。马涛说,深圳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上千万的人,不把这个地方认作家,逢年过节,上千万的归乡大军浩浩荡荡出城而去,深圳顿时变作一座空城。这座平日里奢华浮躁的城市,其实是没有灵魂的。
我知道深圳创立的那段历史,到深圳来的一部分人是被贫穷逼迫来的。那时候,内地农村被贫寒笼罩,很多人是来赚点钱回家盖房娶亲给老娘买棺木的。那时候,我在老家常常能看到一群群背着破被子被人领着上路的闯深圳的民工。我的秘书长是当年深圳的打工者之一。她来深圳的时候,才15岁,她的家在陕西汉中,她说,那时候她家穷得全家人穿不起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且还负债累累。她和妹妹都要辍学了。她的父母留了几夜的眼泪,才决定让她到深圳打工,她和几十个小姑娘被从车窗塞上火车,她被挤压在人缝中,双脚始终无法落在火车的地板上。就这样坚持着,哭泣着,几天几夜,到了深圳。她们被带进一个台湾人开的造鞋厂里。她说,她在深圳一共五年,他始终不知道深圳是什么样子,她只知道无休无止的干活,每月把工资全部寄回家里去。每天计算着春节可以回家的日子。就这样,当这家鞋厂的老板携款逃跑了,她也到了婚嫁的年龄,她才离开深圳回了老家。她说,过去三十多年了,她现在做梦还是梦见在深圳打工,双手还是在被窝了不停地做活。她说她很希望再回一次深圳,好好看看,深圳到底是个啥样子。
据我大概估计,深圳现在有居住证的人口近2000万,曾来深圳打工或者工作,最后不得不返回故乡的可能有七八千万人。这将近一个亿的人口,来自中国内地任何一个角落。在中国大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深圳始终是一个神经中枢,她牵动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这根神经牵动的不只是经济,还有情感。
30年前来深圳的还有一批被一张命令支配来的人,那就是工程兵。据说是工程兵在深圳蛇口炸响了深圳建设的第一炮。这一炮也改变了近一亿人的命运和生命记忆。
1982年,中国裁军100万,这其中,49万是基建工程兵。有史料记载说,
中国军队中自古不缺少能人,这些工程兵很快就适应了没娘管的日子,硬是自己找饭吃了。一个老工程兵告诉我:“这里面有坚持,有离弃,有收获,有牺牲,更有着抹不去的屈辱和荣耀。”据说,有上千名工程兵牺牲在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程兵都经历过发不出工资睡水泥管子,几十人挤在一张通铺上思乡流泪的苦难煎熬。这些人后来大多留在深圳了,但是,他们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深圳人,他们一致的说法是,没办法回去了,户口在这里,房子在这里,再想家也回不去了。还有人更动情地说,只有把骨灰送回去了!
深圳建设的主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自由盲流而来的。他们在一个个工地上找饭吃,饥寒交迫是司空见惯的,赚点钱回家了的是幸运的,把命丢在深圳是常有的事的。马涛告诉我,他认识一对早年在深圳打工的兄弟两,靠给人修墓为生。一天,哥哥病了,还坚持干活,最后死在墓道中。弟弟没有办法把哥哥带回去,也没有钱给哥哥修一个墓地。他就把哥哥直接埋在正在替别人修建的墓道底下。最后,弟弟哭着说,今后没办法给哥哥上坟,但是,只要这个墓地的主人家有人上坟了,哥哥也就享受到香火祭祀了。他的哥哥没有成为深圳人,而变成深圳鬼了。
有一句老话,“黄色娘子军建设了深圳”。在深圳短短30年的历史中,始终离不开妓女这个词,我们现在称为性工作者。她们给深圳留下的记忆,更是叫人感慨唏嘘。当年,深圳建设伊始,大量的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来到深圳,无数的农民工光棍汉来到深圳,这就为深圳开辟了世界上最大的性交易市场。于是,大量的中国内地贫困农村的女孩子们,被各种人引领到深圳,她们大都是乡村贫困人家的孩子,大都明礼仪知廉耻,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把淫乱作为万恶之首的国家,她们为了家人的幸福,毅然解开了自己的裙带,毅然把自己沦落为下九流中的最下流者。任那些陌生的手侵犯她们守护了多少年的贞操,任那些肮脏的病态的各色人物蹂躏她们的躯体,任鸡头盘剥老鸨敲诈殴打辱骂,任警察抓捕追赶。但是,当她们给家乡的父母寄回去她们用血泪屈辱换回来的金钱,想着父母兄妹盖起了房子,穿起了新衣,欺骗父母说自己从事正当的工作的时候,她们的感受该怎样用语言来表达呢?我们常谈论说,在深圳建设时期,许多偏远山区都能收到大量的来自深圳的汇款,而出去打工的男人的汇款数量往往赶不上女孩的百分之一,许多女孩使家乡脱贫,使父母有所养兄妹有所依。后来,又有大量的国企下岗女工及下岗女工的孩子,加入到妓女的行列,使深圳以及邻近的珠海、湛江、广州等地成为所谓的男人的“天堂”,淫乱之名鹊起。我无意给这些妓女们辩护,我只想说,贫穷是这一切发生的根本。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当人民贫穷得衣食堪忧的时候,那些女孩们只能靠出卖自身而自救。在写深圳人的时候,妓女可能是其中最感人的一节。她们也是深圳的建设者,深圳不能忘记她们。当许多妓女人老色衰的时候,她们也只能暗自离开深圳,又有大批的乡村女孩流向这里。我不知道,在妓女们的心中,她们对深圳会是怎样的记忆呢?可能是一张张充满淫欲的脸吧。而深圳对妓女们又会是怎样的记忆呢?
我失散30多年的同学马涛既算是深圳第一批开拓者,也算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是先来的,他的父亲那时是我们礼泉一个贸易公司的干部,是被派往深圳的。马涛那时候和我一起在家乡读书,他是我们班上个子最高最引人瞩目的一个。马涛的才气主要在文学方面,他整天思谋着写小说。三十年之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常常激动地给我讲他构思的小说时的样子,常常讲得眉飞色舞,刀枪不入。他说他要写一篇叫做《田埂上有一双43的鞋》的中篇小说。我忘记了马涛这篇小说写成没有。此后不久,马涛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我们一起落榜。
后来有一天,马涛突然告诉我,他要去深圳,他父亲给他在深圳安排了工作。我当时听了羡慕不已。他有了工作,就像是跳过龙门的鲤鱼,幻化成龙了。他从此不用在黄土地上刨食吃了。
马涛走了,但是还是有消息不断传来,有人讲马涛春节过年没有回家,在深圳的工地上看门,半夜有鬼不断跑到房子中来,马涛就上下楼跑着追鬼,直到把鬼追到海里去了。我虽然不相信有鬼,但是我相信马涛是有胆量追鬼的。此后,我考上陕西师大,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跑来给我说,马涛杀人了,成了死囚。我吃惊得目瞪口呆。
三十年后,马涛给我讲述了他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年,他从深圳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弟。发现母亲和弟弟被人欺辱,他去找人家理论,却被殴打。他情急之下拔刀相向,竟稀里糊涂把人家杀死了。此后,他以伤害罪被判了死缓,在狱中服刑14年。马涛是一个不断制造奇迹的人,他在狱中竟然写出了在全国获奖的小说。因为判刑,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却有另一位姑娘因为读了他的小说而愿意等他出狱再嫁给他,这个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当马涛出狱的时候,他的在深圳打拼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妹妹、弟弟都来到深圳,他们四处打工,再加上父亲留下的一些家底,他们兄妹开创了阔太集团,成为著名服装品牌。如今,他们兄妹都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在深圳房产不少。但是,马涛依然不觉得自己是深圳人,他苦涩地说:“不承认自己是深圳人,也不行了,父亲埋在深圳了,自己也回不去了”。
马涛说得想一个办法,让深圳人对深圳有认同感,能把她当作自己的家乡。第一批开拓深圳的人要么回家了,留下来的正在想办法在老家买墓地。这种身心异处的日子不好过呀!
我和马涛商量,我们杀人无力偷人懒的文人能干什么呢?马涛提议写一首歌说说深圳人。
说起写歌,我马上想起另一个人来,他就是作曲家舒闲。
舒闲原名叫张文立,舒闲这个名字是我前年才为他改的。张文立是西安的一个传奇人物。张文立比我大18岁,他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的,属于前朝的遗少。上个世纪60年代,张文立在西安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上学,正碰上文革。他是典型的多血质,遇上热闹的事情,总会冲进去看个究竟,有时也会直接参与其中。文革时期,张文立在西安音乐学院也曾风云了一阵子,参与辩论,写大字报。但是,张文立却是一个心底纯净脑子简单缺少私心杂念的人。别人在运动中抢官夺权,张文立却是出于纯粹的政治热情。大学毕业后,张文立不经过任何组织批准同意,一个人背了一把小提琴,步行150公里,自己把自己分配到革命圣地延安枣园大队去了。他的心愿就是沿着伟人的足迹,为革命圣地群众服务。但是,枣园的农民却并不认识张文立背来的小提琴是个什么武器,听了张文立演奏了几次世界名曲、《梁祝》之后,群众们把头摇得像电风扇一样,纷纷说,这后生都拉了些没名堂的曲曲,一首正经的都不会。张文立在群众中混不开,不久,延安成立歌舞团,筹办歌舞团的人听说枣园有个会拉小提琴的,便一阵风把张文立接走了。张文立到了歌舞团,就如同鱼儿得了水,有了用武之地,他跑遍延安各地,迅速拉来一帮人,把歌舞团的乐队调教得有模有样。张文立在延安歌舞团一呆就是8年。后来,因为延安的政治风气太硬,张文立和许多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经常成为批判教育对象,有时候甚至有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的危险。于是,张文立决定逃离延安。1975年,张文立在老同学赵季平的帮助下,调回西安市豫剧团工作,后来又折腾到秦腔剧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张文立才再次回到西安音乐学院,在校刊《交响》杂志做了编辑部主任。
张文立虽为布衣,但是却志向高远。他一生都在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一生都想做几件惊动世界的事情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深圳建设发动之后,张文立被老诗人雁翼召唤,停薪留职,跑到深圳来做英国剑桥华人出版公司编辑部主任。老诗人雁翼为人孤傲清高,他只让手下人干事,却不允许任何企业赞助他们的事业,他们本身又没有挣钱的本事。所以,他领的一帮人,开始还人模人样的有几分架子,后来就越发穷困了。张文立从开始租住5000元的单元房,最后竟流落到民工们住的大通铺上去了。但是,就在大通铺上,张文立策划了后来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的大事情。现在打开百度百科,在“和平圣诗”一栏,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两位中国人张文立、雁翼策划了一项轰动全球的创意,全球各国首脑共谱《献给和平的圣诗》。
张文立在大通铺上听着民工们如雷的鼾声,闻着民工们奇臭的脚味策划出来的创意,后来竟惊动了联合国的安南、中国的江泽民、美国的克林顿还有俄罗斯的叶利钦等104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大家纷纷写诗,会写不会写的,都认真地拿起笔,写上一篇,寄给了张文立。于是,《各国首脑献给21世纪的和平圣诗》出版了。而且各国首脑都得到一本。张文立从此名声大振,深圳各家报纸、电视台都采访他。但是张文立依然贫困,依然躺在大通铺上,睁着眼睛做自己的梦。这一次,张文立决定干个更大的事情,他策划了“世界音乐大会”的创意,他要把全世界搞音乐的人召集在一起,像开奥运会一样,来个比赛。他再次写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且迅速得到回应。此后,张文立在广西北海、江苏连云港等地去落实自己的梦想,但是,都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找不到球了。不是支持他的领导调走了,就是资金出问题了。在此中间还穿插着张文立策划中国首次音乐版权拍卖活动,搞得中国音乐家们兴奋不已。但是,就在拍卖活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却被工商部门叫停了。所以,梦想家张文立始终在黑暗中追他那颗遥远的理想之星。
前年,张文立给我讲了他总是临门一脚找不到球的经历,我经过认真推算八字,认为张文立总是处于困境中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名字不吉利,他的名字是大凶之数,所以逢事必败。我的话讲得张文立惊恐万分,他要求我给他重取名字,我就给他取了个新名——舒闲。
此后,张文立以新名舒闲出道,事情果然顺了。2010年底,他让我给二胡独奏曲《秦腔主题随想曲》配歌词,再经过他一番改编,这首叫《大秦川》的合唱歌曲迅速就流行了。文化策划家张文立变成作曲家舒闲了。后来,我和舒闲合作,写了十几首歌曲,舒闲都把曲子谱得优美动听。所以,这一次要给深圳写歌,就得把舒闲请来。于是,我一个电话,舒闲就到了深圳。
舒闲到了深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深圳是我的伤心之地”。他离开深圳,是在他贫病交加,迫不得已的时候,被朋友用大衣裹着绑在摩托车后座上送上火车的。所以,这次他回来,就有无限的感慨。
马涛和舒闲两个在深圳有故事的人聚在一起,说着各自的伤心和感慨。我这个旁听者却是最有心的,他们感慨的时候,歌词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深圳人》这首歌我准备写两个层次的人,一个是庞大的民工和工程兵,另一个就是来寻梦的知识分子们。我想,虽然深圳是伟人在南海边画个圈,才有了深圳。但是真正建起这座城市的是人民,是受尽了艰辛、苦难,也经历了喜悦和收获的人民。想明白了这一切,歌词自然就诞生了:
走出了黑土地,
告别了高原雪,
背上行囊抹着眼泪爬上了火车。
为了母亲住新居,
为了妹妹穿花衣,
披星戴月追着海风来到这里。
大海边,山路多崎岖,
双肩扛起座座桥梁,
磨破多少层皮。
一张通铺上睡着多少好兄弟,
梦中想家声声叫娘枕边洒泪滴。
啊,深圳人,
站在大海边,
双手捧出一轮朝阳讲述一个传奇。
望一眼中原月。
打好资料漫卷诗书挤上了列车,
为了心中的梦想,
为了生命的奇迹。
松开爸爸牵儿的手来到了这里。
高山上,海风吹细雨,
心血化作道道彩虹,
化作大厦林立。
一座小渔村,
变成东方奇迹,
鬓角染霜生命平添岁月的痕迹。
啊,深圳人站在大海边,
任凭青春远去用灵魂守护着你。
歌词写完了,经马涛修改,歌名命名为《深圳人》,舒闲读了歌词,竟泪流满面,是夜,他谱了曲子。
一座城市要记录自己的历史,形成自己的文化,这座城市才是有灵魂的,才会有绵延不断的后续力量,才会让居住在这座城里的人民心灵安妥。深圳也应该这样。作为中国乃至于世界性的大城市之一,深圳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忘记在这段历史中演义人生的人民。深圳应该建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那些曾经为深圳流过泪水和汗水的人,不管他今天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