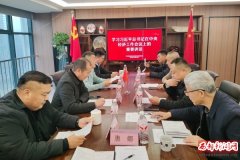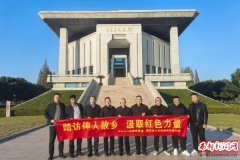作家高建群
西部新闻网讯(记者张栢溪)2018年3月14日,作家高建群悼念霍金 。
高建群说: 悼念霍金,人类失去了最为睿智的一颗大脑。人类也许在新的智者出现以前,会成为一个无头苍蝇。
高建群在《我的菩提树》一书中,曾向霍金这样致敬。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轮椅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扶着轮椅,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两眼空洞无物,茫然地望着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人生有多少机缘,站在这里,向星空仰望!”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
霍金前一阵子,说了一句惊人语。这话叫“科学已死”。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霍金这话,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说给谁的,我不甚了了。不过他的这个句号结构,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写过《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一书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上帝死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口吻,仿佛他是一个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说给霍金,同样合适。
其实这个句式结构,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说:“周礼已死,丘先生难道不知道吗?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们那一堆老骨头,埋在了哪里,现在都无从寻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对这个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相信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这段话就是那个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伟大相遇时,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开头部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老子时任皇家藏书馆馆长),搬上他的牛车,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则用这些典藏,编出《易经》、《诗经》、《礼经》、《乐经》等等六经,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古老智慧。简言之,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
附,《我的菩提树》前言
——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
一本类似遗嘱的书
我的小孙女出生了,她是多么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丛林,她将要从丛林中穿行,开始自已漫长而又漫长的一生。她将要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会是难事,有些事甚至会是些难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经历过许多亊,我遍体鳞伤,我老而不死是为贼。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佑护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这样我决定写一本书,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遇到翻不过去的塄坎时,她打开这本书,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这本书会是一项工程,它大而无当,它试图告诉孩子说,在她出生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都产生过那些古老智慧,等等。
这本遗嘱小而言之,自然是为孩子写的,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我们希望她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
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轮椅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扶着轮椅,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两眼空洞无物,茫然地望着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人生有多少机缘,站在这里,向星空仰望!”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
霍金前一阵子,说了一句惊人语。这话叫“科学已死”。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霍金这话,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说给谁的,我不甚了了。不过他的这个句号结构,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写过《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一书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上帝死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口吻,仿佛他是一个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说给霍金,同样合适。
其实这个句式结构,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说:“周礼已死,丘先生难道不知道吗?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们那一堆老骨头,埋在了哪里,现在都无从寻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对这个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相信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这段话就是那个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伟大相遇时,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开头部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老子时任皇家藏书馆馆长),搬上他的牛车,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则用这些典藏,编出《易经》、《诗经》、《礼经》、《乐经》等等六经,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古老智慧。简言之,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
这话这里不说。现在,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前言”上来。
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说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说过一句令人神往的话,他说,我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岀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在我写作《菩提树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规则地、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正是尼采这一段话。它给我以激励,勉励我用尽自已的全身力气,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
我要规则,我要简约,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起承转换处穿肠而过。我绝不允许拖沓、疲软,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用作参考书的二百本书的内容。
历史是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
记得大约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座谈中,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重写一遍,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
记得我当时有些诧异。我说,二十四史,能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来重写一遍吗?怎么写呢?他说,能写的。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然后,选一个人物,用这个人物的叙事视角,从这件事的中间穿肠而过,这样,事件就写出来了,而人物性格,也因为行动而饱满起来。这样人物也就出来了。
记得,席间,我写了一幅字赠金庸先生,叫做“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后来,电视台导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机场时,金庸先生对郭导说,他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高先生,与他讨论了匈奴民族这个话题——匈奴民族这个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一声消失,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真叫人费解。后来,《文学报》则以“万里怀书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报道的通栏标题。
这本书的这样写作,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张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
这本书的这样写作,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张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
大约1991年,中国作协的一个文学奖在西安颁发,获奖者除我以外,陕西还有贾平凹先生,杨争光先生。张先生则是评委。记得,那天晚上,我陪张先生去西安街头吃夜市。东新街两侧都是红灯笼,我陪着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岁的男孩跟着。
张先生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谈到文学的史诗创作,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要写断代史,把一个民族的断代写出来了,把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就写出来了,云贵川渝十万大山中,生活着十万有苗。这里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家里穷得一贫如洗,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种几棵老玉米,就靠这个为生计。然而,这些民族的女人们,头上却顶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昂贵,华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场大的变故,从而令他们远遁到山里,沦落到今天这个境遇。将那场大变故写出来了,也就是说,将那个断代写出来了,这个民族的史诗也就写出来了。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著名的编辑家,我的《大平原》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先生,也给过一条重要的提示。他说,巴尔扎克说过:历史是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巴尔扎克这话说得好极了,对极了,确实是写过无数好小说的人的过来者之言。一定要有钉子,这钉子要准确得丝毫不差,清晰得历历可见,尔后,所有的小说想象,所有的虚构飞翔,它的出发点、发力点、落脚点都在这颗钉子上。
化大千世界为掌中之物
虽然我努力地这样写,但是我明白《我的菩提树》不是一部小说,或者说不是一部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那种小说。他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体。在这两年的写作过程中,每当向前推进而无法把握时,我就请教案头上的三本书,看它们如何叙事,如何“化大千世界为掌中之物”。
这三本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今人阿诺德 汤因比的《人类与地球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
可以说,《我的菩提树》是这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在这里,作者觉得形式已经退居其次了,让位于内容了。怎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就怎么来——作者想把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如是地表达出来。大概括出来,如此而已。
作者将《菩提树下》的副标题叫做“一部叙事体的东方文明发生史和流变史”,即是出于以上的考虑。
本书内容
这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叫《苏格拉底如是说》。西方古典哲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哪一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
第二部则叫《鸠摩罗什如是说》。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高僧鸠摩罗什,他说了什么呢?他在圆寂时说: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天下的经书,三中有二是我鸠摩罗什翻译的。如果我的译经符合原经旨意的话,火化时舌头不焦。非但不焦,且有莲花从口中喷出。
第三部叫《玄奘如是说》。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高僧玄奘,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僧,他在圆寂时都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早就厌恶我这个有毒的身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该是告别的时刻了。既然这个世界不能久驻,那么就让我匆匆归去吧!
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它用相当的篇幅,对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及流变,遥致敬意。继而,写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生,在这其中,以着重的篇幅描绘了佛教的发生过程。
继而,写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在中华文明板块的伟大相遇。而其中,又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三位佛门高僧,西行求法,广游五印第一人法显法师的故事和传略。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东行长安城草堂寺译经和弘法,他的故事和传略。话本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即高僧玄奘,他的西行求法经历,他的故事与传略。
作者在这里直追道家的源头,直追儒家的源头,直追佛家的源头,描写了它们的发生及流变。而在这块三教合流的土地上,作者眼到手到笔到,对这个东方文明板块饱含敬意,做了一番庄严巡礼,甚至于直达三皇五帝,直达中华文学的伟大源头——《击壤歌》。
结尾
时间在走着,历史的大车轮子在轧轧地滚动。一切都是瞬间,你我皆是过客。
过客的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一个时间段过好,过得有点意义。把我们所能悟到的霍金式的智慧,用诉诸笔墨的方式告诉后人。这应当有点身后遗嘱的感觉吧!原谅我们,我们的智慧有限,思维只到这里!
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马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了。它应当进入它的成熟期了,它应当有它成熟期的标志性作品出现了。《我的菩提树》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另则,好像是希拉里·克林顿说过这话吧!她说,你们永远不要担心中国,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有一天,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它也不会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它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缺少文化,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它没有一本书出现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
这些话叫我们羞愧,叫我们警策。叫我们这些被叫做文化人的人无地自容。哦,但愿这本书,这本名曰《我的菩提树》的书,在变成诸种外文,尤其是英文之后,能叫那些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为它腾一个小小的角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