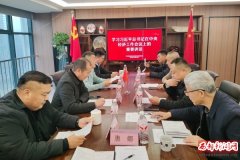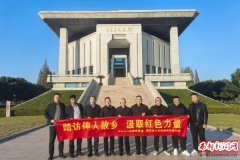车里坐四人,三人基本穏定,只是司机有所调整和变换。
“囯哥”

第一个要说的是“国哥”。他叫孙健,是一位带领粉丝们虚拟旅游的网络大V,网名叫“行走40国”,简称“国哥”。“行走40国”是他走到40个国家时起的网名,现在实际上巳经走了100个国家。他一年四季在地球上快乐地旅行,也带着“国粉们”在网上周游世界。
“国哥”的微博、微信、视频,每次点击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一次旅行下来便是上千万。这次他在合同上签的是千万点击率,行程未过半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万,他说要翻一番,将点击率提升到两千万。听到这个令人晕眩的数字,我兀自矮了半截一一我们这些搞文字的人,青灯黄卷、半死不活累出一本书,印数若能上万,已经是菩萨保佑了,上了十万,没有不得意忘形的。
“国哥”非常敬业,24小时都处于一种工作狂的亢奋状态,此话虽含调侃,却真的不是诳言。他有异于常人的眼光,总能发现新题材奇画面特角度,用最当下最青春最时尚的语言表述出来。他将手里那个自拍杆玩得出神入化,像赵子龙般娴熟利落、花团锦簇。吃住行娱购游,无不收入穀中。
每次停车,第一个消失的人就是他,每次出发,最后一个出现的总是他。车队一启动,他的“体验播报”马上开始了:我是“国哥”,请跟“行走四十国”看世界:这里是我的一带一路行……”用普通话、广东话、东北话连说三遍。一路上又执着地学陕西话说这段开播词,我笑他说的很河南腔,他说他是创造性地揉进了山东腔,还是斗志昂扬地播了出去。
才走三个国家,他一个人已经发了近一百三十条微博视频,全是现场实录。他强调现场感、目击感,善于捕捉悬念,真是个骨子里的好记者。当报道了车队遇到的困难,他会予告:那么下一步这事解决了吗?又怎么解决呢?且听“国哥”下回分解。他的思维很现代,很青春,也很蒙太奇,非常吸引观众。
他常说自己年纪不小了,大家依然把他当小伙子。“国哥”很乐观,总能发现生活中快乐,在自拍杆里做出各种各样轻松的poss。带一个很时尚的眼镜,围一个很时尚的围巾,没事就嗨歌。那些歌对我来说陌生而时尚,却被他内心的快乐而感染。他写过一本书《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希望把艰苦的旅途变成发现快乐、传播快乐、感受快乐的过程,因此极受欢迎,成了青年人的好朋友。
他在广州电视台工作过,但是觉得不能施展自身,便辞职北漂。在央视儿童节目干了一段再度辞职。之后自己独闯江山,终于成为微信网络大V。可不,人生的快乐在于进取,进取的人生才是快乐人生啊!
“国哥”市场意识强,市场影响大,一路上会接到各地的电话,预约下一步的活动。他明确把文事商品化,将自己当作一个品牌来打造。他出售作为品牌的自己,出售自己的传播内容。文化人从中应该得到启发。
“飞哥”

我要说的第二人叫郑飞,是《陕西画报》采访部主任、著名摄影人。70年代后期生人,年轻力壮,承上启下,理所当然被我们选为7号车车长。
郑飞是个有气场的人。高大、帅气、放松,十分本色,这就有了点风度。在生活中,大概属于那类可以依赖的男子汉。我曾经开玩笑说:“郑飞,在行进的车队中,你要当头车,冲在前面开路;在车队遇到麻烦时,你要当尾车,最后收拾摊子;而在摄影业务上,你得成为霸道车,非常敬业,非常自信。这其实是我对70后80后的希望,也是时代加于他们这一代的责任。每逢大活动大场面,几十台摄影摄像机簇拥着噼啪响个不停的时候,常常是郑飞在主宰场面:好,看着这边,onetuothree!一一0k!这不就是整个时代要求他这一代人扮演的角色吗!
拿昨天来说吧,打起早赶到边境,过乌一哈两国口岸,再赶500公里路,车队在路上泡了整整22个小时,郑飞一直作为主驾承担着最重的担子。我们一再让他休息,他总是说“我行,我行”。中间到后座上打了个盹,又回到方向盘前,直到凌晨三点。
他和我孩子是一茬人,是“哥们”,因为有儿子的托咐,对我时有照顾,有时镜头也会偏爱我一点。他一些途中的照片,常常是“内销转出口”,倒是先发给儿子,再由儿子从国内转发我。微信让空间在差异中急速跳转,产生了强烈的蒙太奇感觉。
从郑飞以及他这一代人身上,可以感觉到我们时代七、八十年代这一茬人已经成长,正在成熟,成为社会中坚。在实践和心理上,我们的社会又多了一付可以依赖的肩膀了。
“猴哥”

7号车的第三个成员是小侯,侯明煜,大家都叫他“猴儿”。他是青海电视台的记者,全车队的“珍稀动物”,唯一一个90后。实在很难称“哥”,便叫他“𤠣儿”。90后的“猴儿”却少言寡语,说起话来声音也很小,实在看不出多少“猴”劲儿。唯一的一次大声,是他给家里打电话,信号不好,对方听不清反复问他是谁,他急了,大声喊:我是你儿子!让人笑出了声。
小侯不幸荣获了这个“猴儿”的称谓,一是因为姓,二是因为爱,小弟弟嘛。别看他悄悄地不吭气,车里车外的事,跑腿,搬运行李,管理车钥匙,打扫卫生,都是他在默默的干着。这个小弟弟腿勤、眼到,被我们擢升为副车长,车长不在时,代行车长职权。货真价实的革命接班人!
车队这次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坐到一个车上,作一些文化对话,好拍摄电视连读报道中的《丝路云履》专栏。一进入业务领域,沉默寡言的九零后就显出了主见。他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修正我的想法。
有次聊天,偶然提到哲学,小伙子出乎意料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喜好哲学,曾经在图书馆里硬啃过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一星期只读了8页。山东大学
毕业,报考的就是哲学博士,后来却到电视台当了编导。我们谈共同喜欢的作家杨志军,谈他作品的哲学内含和生命内力。我们谈刘朗电视片的文化思考,谈诗人昌耀,谈燎原。后来又谈阅读的乐趣。我们都更喜欢纸质书,觉得电子阅读像是查阅电脑目录去借阅公共图书馆的书。那是别人的书,只有读自己书架上的书,知识好象才归自己所有。我还想说:天下的好风景虽多,大都是别人的风景,有时真不如自家门前的小街小巷,吃喝拉撒睡都在其中,才是自己的人生。……但已经嚷嚷着叫下车办签证了。
在这个把哲学挤到旯旮拐角的时代,哲学之光竟然这样点燃了一位年轻人的心,“猴哥”之幸,哲学三幸呀!
东干哥

在长途跋涉中,我们车里还短期轮换了两个从中国迁到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族的司机艾迪尔和白二山。他们祖上都是陕西,不需要翻译相互能够简单交流。为了文章的体例,姑称他俩为“东干哥”吧。
一个叫艾迪儿,小伙子长得很标致。中国人熟悉的面庞上嵌着中亚人的深眼窝。他在陕西读了好几年书,中文表述很好,给我们介绍了不少中亚的情况,是那种有涵养有知识的青年绅士形象。
一个叫白二山,已经六十岁了,汉语混搭着俄语乌语,交流起来有一点隔阂。但有几个词我每天都问他,他都会爽快的回答。我说瞌睡吗?他说不瞌睡。我说吃了吧,他说吃了。我说端走,他说好,端走。话不多但是心里有着依恋。在塔什干,他带我们去郊区东干村自己家里。大儿子和他住一起,很出息,是个公司的销售经理。他把他大哥三弟全叫来,让我们较全面的了解了一个中亚东干族的家庭。
白一山开车千里送我到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布哈拉,路上打电话联系什么,原来他第二个孩子在布哈拉工作,中午我们吃饭时,老二一家会来看我1们。爷爷对子孙的关爱溢于言表。在布哈拉吃饭时,儿子一家果然开着车,带着儿媳妇和两个孙女来了。爷爷抱着小孫子又亲又逗,活脱脱就是一位“中国爷爷”!我们合了好几张影。
白二山让我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中华生命,在异域的丝路上如何生存发达。你感觉到了人生的温度。
老汉我

7号车最后一个乘客就是老汉我自己了。在一个征程万里的车队中,完全不会开车,又因为年长,处处优先,处处受照顾,我心生着天然的惭愧。其实,人活到了处处受照顾受优待的地步,心里是別有一种况味的。
大家都这么忙碌这么抢着挑担子,坐在副架位置上的我,能干什么呢?只能当好服务员。内心的不安使我经常问司机:喝水吗?吃苹果?馕呢,要不?再有就是陪聊,怕旁边的司机磕睡,怕他疲惫,得用各种各样的话题和司机聊。有时甚至殷勤到主驾郑飞有了感觉,说:你休息,不用有意找话题跟我聊,我能行,精力好着呢。我于是很愧疚的默下了声。过一会又开始了,聊天,倒水。这就是我在车上的主要工作:服务和陪聊,同时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给大家添麻烦。我曾向车队王大夫表示,力争一路上不找他挂号开方子,给医学做一个80老汉跑万里丝路的案例,回去好好谢他。他说,老爷子那我得谢你!
赶夜路的时候,后面的两位是可以轮流打盹的。但副座上的我可不敢眯糊,一定要醒着,和主驾不停的聊天,别让他瞌睡。所以我也挺辛苦的,从头到尾都得睁着眼睛说话呢。有什么办法呢,我年龄大,瞌睡少,忧虑又多,“舍我其谁”?
我犯过一次错误,必须记录在案,以儆效尤。车队曾宣布严禁向车窗外扔垃圾,违者罚款一百美元。不幸的是,之后的某次夜行中,我下意识朝外扔了个纸团,当即被后车发现,在车台中追问,我当众承认,表示停车即交罚款。曾想将罚款发手机红包,让大家娱乐一下,但那有违纪律的严肃性,还是第二天早餐时郑重地将罚交给了领队。
这就是我们的车队,我们的车。一个老汉三个哥,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性格,职业,出身,经历,在追寻玄奘的艰苦的丝路上融汇成一个有趣的小社会,一个小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有难同当,有饭共咥,有快乐一起享用,有困难一道克服,这个小家庭真是温馨,好温馨。(2016年10月22日于哈萨克斯坦里海之宾旅次)